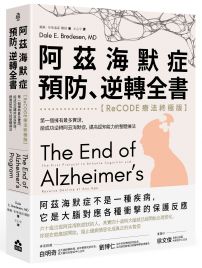第一章 新型疫苗
妮娜來找我是為了「預防阿茲海默症」,她說她的祖母從一九六○年代開始失智,她的母親則在年僅五十五歲時,發現自己說話時總想不到正確的詞,還喪失了簡單運算能力,例如計算小費應該給多少。之後情況開始惡化,被診斷出阿茲海默症。妮娜想避免同樣得到這個疾病。她先前從專家口中得到的標準說詞是,「沒有任何方法能預防、逆轉或延緩阿茲海默症」。
如同七千五百萬美國人一樣,她帶有一組阿茲海默症風險基因ApoE4 序列。她的ApoE4 基因很有可能是從外婆和母親遺傳來的,此基因大概也是她們開始失智的最大遺傳性因素。妮娜過去也被診斷出體內的維生素B12 偏低、維生素D 也低。
雖然她只有四十八歲,基本上無認知障礙主訴,只覺得自己總是「愛操心」,但是她的MoCA 評估(蒙特利爾認知評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的縮寫)分數卻不理想。這是一種簡單、快速的篩檢測驗,用來評估各類型的大腦功能,如記憶力、組織能力、運算能力,以及語言能力。MoCA 評估滿分是30分,大部分的人會得到28 至30 分,但妮娜只得到23 分,表示她已經有輕度認知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也就是阿茲海默症的前期。後續的神經心理測驗,也確認她罹患輕度認知障礙,表示她已經開始走上母親與外婆不幸發展成失智症的道路了。
她開始加入我和我研究團隊發展出的「ReCODE」(reversal of cognitive decline,意即逆轉認知退化)療程。幾個月後,她發現自己有了很大的改變。她說:「開始康復之前,我完全沒發覺我原本的思考能力變得有多糟。」最後她在MoCA 評估裡得到滿分30 分,之後也持續保持這樣的進步狀態。她發電子郵件給我:
「非常感謝您給我機會參與這項療程。這真的救了我一命,我會永遠感恩。」
你或許在想:「妮娜確實改善了,但那是因為她只是早期的認知衰退。萬一她已在阿茲海默症晚期會怎樣呢?」讓我分享克勞蒂亞的故事吧。
克勞蒂亞是一位七十八歲的女性,有認知衰退,最後發展到重度阿茲海默症。她當時MoCA 的評估分數是零分。她無法交談,只有偶爾迸出「是」或「不是」。她無法騎腳踏車、無法自己穿衣服,也無法照顧自己。評估她之後,我們客製出一個計畫,針對誘發她認知衰退的因素進行一系列療程。她的評估指出有一些之前未被察覺到的誘發因素,包括因黴菌所產生的黴菌毒素。雖然她的基因檢測呈現陰性,卻顯示有胰島素抗性。她的主治醫師是優秀的瑪莉.凱.羅斯(Mary Kay Ross)醫師,專門治療有生物毒素(biotoxin)暴露的病患。她的治療包括,避免接觸誘發物,讓排毒機制最佳化,調整個人化飲食,也開始採取各種不同的突觸(synaptic)支持性療法。開始這樣的治療時,克勞蒂亞的狀況時好時壞,然而,歷經四個月後,她的狀況開始改善了;她漸漸恢復說話能力,重新開始寫電子郵件,能自己穿簡單的衣物,騎腳踏車,甚至與丈夫共舞。
她的先生寫信給我們說:「今晚,我們出門散步時,她謝謝我帶她出門,讓她能觀察周遭事物。她指出許多事物,包括夕陽餘暉下的粉色雲朵。後來我們坐在一起聊天,我念了每一篇部落格文章給她聽,向她解釋每一步我們都經歷了什麼。她就跟我說:『看來,我以後應該沒問題了,也能再度享受生活了。』」
我要先提醒一下,克勞蒂亞的狀況其實是個例外而不是常態;一般而言,愈早開始進行這套計畫,成效可能會愈好,反應也可能更完整。如同從克勞蒂亞的案例中看到的,即便症狀到了很晚期,最後狀況都還是確實有改善。再說,這樣的進步,乃至於任何形式的進步,在幾年前都還是連想都不敢想的,對許多仍在追求標準化、單一藥物治療的人而言,更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讓我們再回頭談談妮娜的情況:妮娜目前仍繼續採取這種二十一世紀形式的阿茲海默症「新型疫苗」,也就是一種個人化的精準醫學計畫,針對造成阿茲海默症的生化參數(biochemical parameter)進行分析與處置。這個二十一世紀的「疫苗」不只能預防,還能在早期逆轉疾病,這可是二十世紀注射式疫苗做不到的事。且不僅如此,除了預防與逆轉,它更能強化任何年齡層的認知能力。不論你是四十幾歲、八十幾歲,甚至是二十幾歲,利用這裡所描述的計畫,都能加強你的認知能力、讓你的注意力與工作能力達到最佳、增強記憶力,並且改善說話的能力。
妮娜的經驗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認知衰退往往是偷偷上身。諾貝爾獎得主理察. 費曼(Richard Feynman), 他被喻為二十世紀後半的愛因斯坦,就曾因為硬腦膜下血腫(subdural hematoma,一個擠壓到腦部的血塊)出現認知衰退的症狀。血塊被移除之後他的聰明才智都回來了。他當時就說,自己往往很難察覺到自己的認知開始衰退。這些複雜的慢性疾病就像一條大蟒蛇,當牠們纏住你時,你可能很多年都沒感覺到牠正在勒著你⋯⋯但牠會一圈一圈地纏繞住你。你可能偶爾感覺自己老了,或是忘記自己車子停在哪,但你又會覺得,大家不都是會這樣嗎?即使是醫師也看不出這緩慢進行的收縮。直到你罹患末期絕症了,一切都已太晚。
不過,這裡有個好消息:複雜型疾病的阿基里斯腱我們在發病前好幾年就能看到它的徵兆,因此我們有很多時間可以預防(好啦,我知道大蟒蛇沒有腳跟,但你知道重點是:我們可以及早克服這些疾病),只要我們有心觀察。
如果我們的醫師未能適當地評估、預測並預防認知衰退,我們也就無法採取關鍵的預防行為,這會導致我們許多人──「噢,我們知道問題在哪,這很常見。這就是『車子壞掉症』,老車很常出現這樣的毛病。沒有人知道原因,也沒有辦法修好──你的車子就要報銷了。」當你眉頭一皺,繼續問這位專家,他會不會做些檢測來判斷發病的根本原因,專家會回答:「不會,我們不做那種檢測,因為健保不給付。」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建議,就像我們都知道年過五十歲要去照大腸鏡一樣,年過四十五歲就要(或是過了這年紀就盡快)進行「認知鏡檢查」(cognoscopy)──這是一套血液檢測與一項簡單的線上認知評估測驗,讓我們知道該如何預防認知衰退──才能讓阿茲海默症成為罕見疾病,因為它本該如此。
所以,讓我們來看看阿茲海默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該如何認識它,為什麼它這麼普遍,以及最重要的,我們能如何預防並確實逆轉認知衰退、保持治療後的進步狀態,如同我們好幾百位完成療程的病患那樣。我與實驗室同事們已經研究這疾病超過三十年了。二○一一年,我們提出第一個阿茲海默症的全面試驗。我們研究的結果顯示,我們必須針對誘發疾病的多重因素進行評估,才能著手處理觸發疾病的隱形因素,而不是採取一般的單一藥物(monotherapy)療法,因為那種療法不斷失敗。不幸的是,這項試驗被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IRB)拒絕了,因為他們認為療程太複雜,也未遵循只測試單一藥物或療程的標準。我們的反應當然是告訴他們阿茲海默症不是單純的單一變因疾病,因此不適用標準的單一藥物治療方式。可惜,我們的抗議無效。
我們多年來的實驗室研究為什麼會歸結出這麼非典型的療程呢?因為我們發現一個真正的範式轉移,一個能改變我們預防並逆轉認知衰退(以及延伸出來的其他神經退化疾病,還有大部分的慢性複雜型疾病)的方式──不是單顆的銀彈,而是銀霰彈。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與阿茲海默症有關的理論非常、非常多;有人說是因為自由基或鈣,或鋁,或汞,或類澱粉蛋白(amyloid),或濤蛋白(tau),或普利昂蛋白(prions),或是因大腦的糖尿病(第三型糖尿病),或是細胞膜破壞,或是粒線體(mitochondria,細胞的能源中心)損傷,或是腦部老化等等,各種觸發因素族繁不及備載。但沒有任何一種理論能提供有效的治療方式,即使我們花了上兆美元進行臨床試驗與藥物研發。
相較之下,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了預防及治療阿茲海默症的方法:阿茲海默症的核心是一個分子開關,稱作「類澱粉蛋白前驅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以下簡稱APP),從腦細胞表面突出。APP 會根據其所處環境,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請把自己想像成「大腦共和國」(MyBrainistan)的總統。當你的國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時,國庫充盈,沒有失控的通貨膨脹,也沒有天大的汙染災難要處理;天時地利人和,所以你要為自己的國家興建並維護基礎建設。因此,你發出適當的行政命令,興建新大樓,發展出新的互動模式,國家網絡也隨之擴展。這就如同發生於你大腦的狀況,當你的腦部獲得充足的營養、荷爾蒙與生長因子(所謂的國庫充盈),身體裡沒有病原體或相關的發炎症狀(沒有在打仗),你也沒有胰島素抗性(失控的通膨),也沒有暴露在毒素之下(沒有重大的汙染)的時候。此時,你的APP 會發出滋養信號,這個信號是利用一種稱為「蛋白酶」(proteases)的分子剪刀(molecular scissors),在APP 一個特定的α- 位置下刀裁剪,進而產生出兩個有滋養與維護功能的片段(peptides,稱為「胜肽」):sAPPα與αCTF。這時候會發出「成突觸」(synaptoblastic)的訊號(希臘文的「發芽」或「產生」),也就是下令製造大腦裡掌管記憶力與整體認知的神經元突觸(連結)。
現在,再試著想像,你在「大腦共和國」第二任期時,局勢有了改變。國庫開始吃緊,所以你不能繼續建造或修葺基礎建設;入侵者跨越邊境,所以你發射汽油彈殺死進攻的敵人;平和時期發生的通貨膨脹,讓財政部要花更多錢才能資助經濟成長;脆弱的基礎建設導致汙染變得嚴重,所以你還需要清理這些汙染。這就是腦部罹患阿茲海默症時,以及認知衰退開始、直到演變成全面性的阿茲海默症時的情況:缺乏營養、荷爾蒙與滋養因子的支持,因此需要開始縮減;那些與阿茲海默症直接相關的類澱粉蛋白,就是用來抵抗微生物與發炎碎片的物質,它們簡直就像燒夷彈般堅壁清野;胰島素抗性的意思則是,身體分泌的胰島素無法有效讓神經元存活(胰島素一般是腦細胞強而有力的支援分子,在培養皿培養腦細胞時,要確保細胞的健康與活力,胰島素是必不可少的);如汞之類的毒素,也會緊緊被類澱粉蛋白束縛。為了對抗這些攻擊,APP被裁剪的部位就會不同,不是位在狀態良好時的α-位置,而是會在另外三個部位:β-位置、γ-位置、凋亡蛋白酶位置(caspase site)。因此會產生四個胜肽片段。你可以想像這四個片段(就像《啟示錄》中的末日四騎士),會發出縮減而非滋養的訊號。這叫做「破突觸」(synaptoclastic,來自希臘文中的「破壞」)訊號,會使腦部失去突觸。
再讓我們回到大腦共和國,你可以想像自己又選上第三任期的總統(對,大腦共和國可以連任三次!),但你的國家已經一分為二,變成北大腦共和國與南大腦共和國,你可以選擇當其中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你會想選哪一邊呢?北大腦共和國是一個好戰的國家,他們決定把資源用在防禦(以及發動攻擊),而南大腦共和國則把資源放在研究與發展。因此,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優勢與劣勢。這就是遺傳影響阿茲海默症罹患機率的方式:雖然有許多基因會影響患病的風險,但是最常見的遺傳風險是一個獨特又奇妙的基因,叫做ApoE基因(載脂蛋白E)。你有一對基因,一個來自母親、一個來自父親,你可能沒有ApoE4這種高風險基因;也可能你只有一個,或是有兩個。美國將近四分之三的人、近二.四億的人口沒有這個基因(我們大部分的人是ApoE3/3,意思是有一對ApoE3基因、零個ApoE4基因),這樣我們一生當中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機率是百分之九。然而,將近四分之一,也就是超過七千五百萬人,有一個ApoE4基因,導致一生中患病機率大概會變成百分之三十。最後,我們少數一部分的人(只有大約百分之二,或少於七百萬美國人)則帶有一對ApoE4基因,因此一生有很高的機率(超過百分之五十)發展出阿茲海默症。本書Part II會分享茱莉的經驗;她是一對ApoE4基因的帶基因者,也出現過重大的認知衰退症狀,但她現在的恢復狀況讓她能為本書貢獻非常寶貴的資訊。
如果你帶有ApoE4基因,你就是北大腦共和國的領導人,你會把資源都用來抵禦外敵,因此能防止入侵者侵犯領土。帶有ApoE4基因的人能抵抗寄生蟲與其他感染源,因此在骯髒的環境下更有生存優勢。事實上,據說讓我們祖先,那些早期的原始人類,從樹上下來、行走在稀樹草原,腳底被扎著卻沒有被感染導致危及性命,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與ApoE4基因有關的抵抗力。這點與ApoE4曾是原始人類最原始的ApoE基因的論點契合。直到二十二萬年前ApoE3基因才出現。換句話說,我們的祖先都是ApoE4⁄4的帶原者,我們從原始人類演化至今,百分之九十六的時間都是這樣的基因樣貌。人類有能快速對抗發炎的反應能力,雖然對於吃生肉、療癒傷口是好事,但是經年累月之下,身體的代價是,我們罹患發炎症狀相關疾病的風險增加了,例如阿茲海默症與心血管疾病。
如果你沒有ApoE4基因,你會是南大腦共和國的領導人。你會把資源放在研發與發展上(也就是較少發炎、代謝比較有效率,也更長壽)。不帶有ApoE4基因的人,比較難對抗掠食者如寄生蟲的入侵,但如果能避開這些外憂,讓發炎程度較低,等於是讓罹患阿茲海默症與心血管疾病的機會也較低,平均壽命也會多幾年。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稱之為阿茲海默症的疾病,其實是一種保護反應,用來回擊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例如微生物與其他炎症刺激物(inflammagen)、胰島素抗性、毒素攻擊,以及缺乏營養、荷爾蒙與滋養因子支援的情況。這是一種保護性的組織精簡計畫。換句話說,阿茲海默症是腦部在撤退,腦部的焦土政策。隨之而來的認知衰退是可以預防或逆轉的,只要我們處理造成「成突觸」與「破突觸」訊號不平衡的因素。我們最近發表了一份醫學報告,描述一百位病患的狀況;有些已罹患阿茲海默症,有一些則在阿茲海默症前期,但所有病人最後都顯示出有紀錄、可量化的進步。不只認知能力提升了,有些病患也照了可量化的腦電圖(EEG,可測量腦波速度,會隨著失智症進展而減慢),結果顯示狀況有改善;他們也進行了容量分析核磁共振造影(能偵測腦部各部位萎縮情況),同樣也出現改善情況。這不是說每一位進行此療程的人都出現良好反應,但我們記錄到前所未有的進步,更重要的是,採取這個精準、有規劃的計畫之後,這些進步都能持續。
究竟要如何將這些概念轉化成一個可以採取行動,而適用每個人的計畫書呢?本書就是要說明此事。你會在此讀到所有需要的細節,以採用適合個人而且有目標的認知功能提升計畫。無論你決定與醫師、健康教練等醫療專業人士合作,或是自己行動都可以。(本文經摘譯,完整全文請見書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