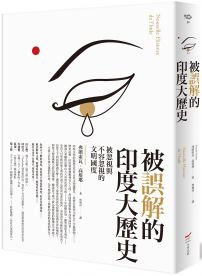第2章 消失的薩拉斯瓦蒂河
自千年以來,主要河流從喜馬拉雅山脈流下,流往旁遮普邦(Pendjab)、哈里亞納邦(Haryana)和拉賈斯坦邦。位在印度次大陸的這幾個邦,因河流流過而綠意盎然、土壤肥沃;但現在,這些邦裡絕大部分都成了沙漠地帶,如拉賈斯坦邦。所有偉大的文明都在主要河流兩岸發展繁盛,因為河流可以調節氣候、灌溉田地,還能當作運輸航道,並且帶來飲用水源。在《吠陀》四卷(梨俱吠陀﹝Rig-Véda﹞、夜柔吠陀﹝Yajur-Véda﹞、娑摩吠陀﹝Sama-Véda﹞、阿闥婆吠陀﹝Atharva-Véda﹞)、《往世書》和《摩訶婆羅多》(Mahabaratha)那樣的印度古老文本中,都經常提到一條名「薩拉斯瓦蒂」的河流;這條曾被提及千百次的河流,似乎就屬於本章開頭敘述的那類型河流。
印度教徒把河流當作女神崇敬,而薩拉斯瓦蒂河就是象徵工作完成及圓滿的女神。
《梨俱吠陀》中以敬重的語氣提到薩拉斯瓦蒂河五十多次,並以「極優秀的母親、極優秀的河流、極優秀的女神」形容薩拉斯瓦蒂河。在《梨俱吠陀》著名的讚歌〈河流頌歌〉(Nadi Stuti)中,也同時提到了恆河、亞穆納河(Yamuna)、薩拉斯瓦蒂河、薩特萊傑河(Sutlej);從中還可以得知,薩拉斯瓦蒂河的地理位置在亞穆納河和薩特萊傑河之間。在讚歌中也說明了薩拉斯瓦蒂河的起源,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薩拉斯瓦蒂河是極為純潔的河,充滿動力,自山間流向海洋,而且不吝於將河流廣大的資源帶給眾人」。另一首讚歌也詠唱薩拉斯瓦蒂河的力量:「此河中的浪強勁壯烈,分裂山峰如摘折蓮花般易如反掌……」。
長久以來,薩拉斯瓦蒂河一直被視為傳說。雖然從一八七二年起,就有C.F.歐德漢(C. F. Oldham)與R.D.歐德漢(R. D. Oldham)對薩拉斯瓦蒂河及其支流可能流經的地區展開詳細研究,他們證實找到了薩拉斯瓦蒂河的水道位置。兩人所下的結論是:「薩特萊傑河和亞穆納河曾經供給薩拉斯瓦蒂河水源,薩拉斯瓦蒂河先向西遷流,之後又往東,接著就消失了。」
直到一九四○年,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在古時的巴哈瓦爾布爾土邦(Bahawalpur)境內發現了乾涸的薩拉斯瓦蒂河部分水道,在當地被稱為「哈卡拉河」(Hakra),河的兩岸共有九十多個遺址。著名德國地理學家赫伯爾特.威廉密(Herbert Wilhelmy)在一九六九年研究相關地區之後,也得出以下結論:在地形產生變化之後,亞穆納河改變了水道方向,薩拉斯瓦蒂河因失去水源而乾涸。
時至今日,最新的考古發現和科學衛星影像的技術,重建了薩拉斯瓦蒂河的誕生與消逝;結果顯示,薩拉斯瓦蒂河比印度河要更寬、更深,印度河卻在現代歷史書裡占了主要篇幅。薩拉斯瓦蒂河發源於本德爾本傑山(Bandarpunch),此山位於現今的加瓦爾(Gharwal)專區,是境內喜馬拉雅山脈的一大高峰;薩拉斯瓦蒂河向下流經阿迪巴鐸(Adibadri)、巴哈瓦爾布爾土邦、巴爾夏布洪(Balchapurand)一路流進平原後轉往西,流過今天的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拉賈斯坦邦與古吉拉特邦(Gujarat),最後從古海口「大卡吉鹽沼地」(Grand Rann de Kutch)流入阿拉伯海。薩拉斯瓦蒂河似乎因西瓦利克(Siwaliks,又稱「外喜馬拉雅山脈」)山麓丘陵板塊移動, 在西元前五○○○年開始枯竭。
事實上,西瓦利克山脈整體自巴基斯坦的博德瓦爾(Potwar)高原延伸,直到印度阿薩姆邦內,並從更新世(約一百七十萬年前)就開始移動;可能就是在移動過程中使薩拉斯瓦蒂河與供養水源的冰川分離,因此薩拉斯瓦蒂河僅仰賴季風雨水供應水源,最後逐漸乾涸,至西元前三○○○年完全消失。衛星圖像則顯示出目前克格爾河(Ghaggar)的河道,與昔日薩拉斯瓦蒂河的河床大致重疊。以碳、氧同位素檢測克格爾河中的沙粒,結果皆顯示此區在更新世中期時受到溫帶氣候影響,曾有大量水源,甚至經常性氾濫。
因此,薩拉斯瓦蒂河與印度河是吠陀文化時期最重要的兩條大河,而幾條今日仍存留的支流雖然已偏離原本河道,還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印度河支流、亞穆納河、格傑赫姆河(Ghjulm)、奇納布河(Chenab)、薩特萊傑河及克格爾河。
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境內近期的探察中,於印度河與薩拉斯瓦蒂河流域鑑別出超過兩千處屬於哈拉帕(Harappa)文明的遺址;而在薩拉斯瓦蒂河流域所鑑定出的遺址數目,遠比印度河流域要高出七倍左右,因此令人不禁猜測:薩拉斯瓦蒂河流域對哈拉帕文明的形成,有著較多且重要的貢獻。薩拉斯瓦蒂河流域的總面積約為兩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一路向北方的羅巴爾(Ropar)行政區延伸,南至哥達瓦里河(Godavari)畔的丹納貝德(Dainabad),東往欣登河(Hindon)畔、近德里的阿蘭吉布爾(Alamgirpur),西至近阿拉伯海的蘇特克根多爾(Sutkagendor)和迷利卡拉特(Mirikalat)兩處考古遺址。
透過遙測與地質同位素等科學方法研究,再加上開挖發掘,能更精確地重建薩拉斯瓦蒂河的歷史。印度衛星IRS-1C結合了歐洲遙感衛星的雷達影像,其所拍攝的照片可鑑別出,在拉賈斯坦邦的塔爾(Thar)沙漠中可見薩拉斯瓦蒂河現今仍存留於地底的部分。
另一項衛星研究也證實了在印度河與薩拉斯瓦蒂河之間,曾經有過一條天然的水渠,由此也確認了這兩條河流當時相依互存的情況。今日,拉賈斯坦邦的比卡內爾(Bikaner)、岡格阿納加爾(Ganganagar)和賈沙梅爾(Jaisalmer)等地為乾燥地區,地質學研究為了找出可飲用的水源,發現了幾處地下河區域,這些伏流與喜馬拉雅山脈的冰川融水毫無關聯,反而是延續了薩拉斯瓦蒂河殘餘的部分。位於焦特布爾(Jodhpur)的中部乾旱地帶研究所(Central Arid Zone Research Institute)中,有三位科學家組成團隊,並藉助陸地衛星影像圖廣泛研究此區,他們在研究報告中做出結論:「我們認為薩拉斯瓦蒂河造成了沙漠最西端的沉積,而這部分地下水的主要水源和幾世紀以來滲入地層的沉積,皆與薩拉斯瓦蒂河相同。」為了證實這個說法,中央地下水委員會(Central Ground Water Commission)在乾涸的河床上鑿了二十四口井,結果發現其中二十三口井產出可飲用水。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月,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Bhabha Atomic Research Centre)在波卡蘭(Pokhran)進行核試驗後(由印度私下進行,而後被歐洲與美國判罪),進行了一系列的測試,以評估當地與周邊地區的水質;測試結果證實此區的水可以飲用。來自喜馬拉雅冰川的水源歷史悠久,可回溯至西元前八千到一萬四千年前,儘管北部少雨,之後仍逐漸由北方的含水層持續供應水源。這個推論鞏固了薩拉斯瓦蒂河曾存在的事實,因此今日稱之為「消失的薩拉斯瓦蒂河」。
第4章 雅利安人入侵迷思
在十八到十九世紀之間,語言學家注意到梵語和大多數歐洲語言驚人的相似程度,於是得出結論:梵語和歐語之所以如此類似,是因為源於同一種語系,語言學家稱之為「印歐語系」。十九世紀時,英國率領工業發展,在殖民者心態下,這群語言學家也想像出西方在西元前一五○○年左右對印度的侵襲。人們對傳說中征服印度原住民的「雅利安入侵者」多有著墨,說是他們規定使用梵語,並以吠陀文化原形和不平等的種姓制度取代當地傳統,而這樣的文化後來漸漸傳布至印度北部的恆河平原。雅利安人入侵的說法在某些人看來,是英國殖民印度的正當理由,一如梵語學者威爾森(H. H. Wilson)在一九五八年寫道:「雅利安大家族以特定方式團聚,旨於發展印度文明和提倡基督教。」
然而,這種說法不是人人都認可,知名英國生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就不認同語言學結合所謂雅利安家族的說法。語史學家艾薩克.泰勒(Isaac Taylor)則認為,雅利安人入侵的推論建立在疑點重重的基礎之上。印度獨立的重要人物,如斯瓦米.維韋卡南達(Swami Vivekananda)、斯瑞.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和阿姆倍伽爾(Ambedkar,印度憲法之父)等人,都說雅利安人入侵這個眾所皆知的推論,從未出現在任何印度的古籍中,而且認為歐洲梵語學者有意曲解印度古文的翻譯,好佐證他們自己的推論。
印度考古考察部總監約翰.馬歇爾在發現印度河-薩拉斯瓦蒂河流域文明之後,在一八五六年對雅利安人的歷史第一次提出質疑,馬歇爾在書中寫下:「從前我們認為在前雅利安時代的人,文化程度尚未開發,然而現在卻發現西元前四○○○年時,住在摩亨佐-達羅城和哈拉帕城的人們,擁有比我們更先進的文明。」照這個說法看來,印度當時的原住民倒成了文明人,而入侵的雅利安人反而是半開化的遊牧民族。儘管有上述的反面看法,所有印度歷史書籍仍以雅利安人入侵的推論做為基礎闡述。
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在一九三四年指出:「我們在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都沒有找到兵器遺跡,連在陶器上都沒有發現描繪戰爭的圖像;這與古埃及和巴比倫相反,它們在被殘暴地結束文明時,都留下了考古遺跡。」
支持雅利安人入侵理論的人仍持續辯駁,說摩亨佐-達羅的防禦城牆極厚,「由此可看出他們對入侵者的恐懼」。然而美國考古學家肯諾爾反駁說:「我們從未在防禦城牆上發現由戰爭所造成的缺口或裂縫。」雅利安人入侵理論的狂熱支持分子還提出另一項討論:在摩亨佐-達羅找到的骸骨上可見傷痕,他們一定是「在雅利安人入侵時被刺傷或殺死的」。不過近期以碳14定年法檢測結果卻顯示,這四具骸骨處於印度河-薩拉斯瓦蒂河流域文明中的另一個時期,而在骸骨上發現的傷痕早在死亡之前就已癒合……
美國考古學家喬治.戴爾斯(George F. Dales)是肯諾爾的導師,他也曾寫下:「在摩亨佐-達羅末期並未有毀滅的跡象,甚至連火災的痕跡都沒有;大規模的挖掘結果也沒有找到穿著盔甲的士兵骸骨,更沒發現骸骨旁葬有戰爭兵器。我們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有出兵征戰,或所謂雅利安人入侵造成毀滅的事實。」
雅利安人入侵論的支持者,現在也開始讓步,用「遷徙」這樣的字眼來代替「侵略」,意指溫和的遊牧民族因遷徙而將印歐語言引進印度。不過,就算換個說詞,在薩拉斯瓦蒂河或印度河河岸,都從未發現雅利安人「溫和」入侵的考古遺跡。法國考古學家讓.瑪希.卡薩勒(Jean-Marie Casal)曾在哈拉帕另一處遺跡蒙迪加克(Mundigak)指導挖掘工作,他強調說:「考古學上沒有對雅利安人的定義,因為我們並沒有發現任何與哈拉帕文明不同的物品或武器。」
哈拉帕文明和後哈拉帕文明之間,不管在宗教心靈或文化方面都沒有斷層,與雅利安入侵論支持者長期以來的說法相左。不過,在這兩個文明時期都有對辯才天女、濕婆的林伽和約尼(女性生殖器的神聖象徵)相同的崇拜。也因此,研究摩亨佐-達羅的專家馬歇爾認為,哈拉帕文化「十分具有印度特色,很難與現今仍奉行的印度教做區隔。」同時身為考古學家的馬歇爾是在一九三一年發表了以上意見,但這句話到今天仍然適用。
近期的研究也顯示出雅利安人侵襲假說,屬於人類學和遺傳學的範疇。長期以來,一般的確都認定雅利安人的皮膚比達羅毗荼人(Dravidien)明亮,而達羅毗荼人膚色偏黑;因此以雅利安人侵略論區分印度人種的膚色,分成膚色較白的婆羅門(祭司)和剎帝利(軍事貴族,與摩訶拉者﹝maharajas,帝王﹞屬於同階層),以及膚色較深的賤民與種姓層級較低的人。即使到今天,在政治上仍藉由雅利安人侵略論來左右選舉;例如,坦米爾納德邦的政治人物就對強制使用印度語有所抱怨,他們認為印度語是梵語的分支,也就是屬於「雅利安語支」。一九八○年代在坦米爾納德邦甚至有騷動抗議事件,反對強制使用印度語。時至今日也一樣,為了使賤民、部落和種姓低階人民皈依基督教,聖公宗的傳教士(主要來自澳洲與美國)對他們說:「你們才是印度真正的居民,比雅利安人還要早到來,因此你們與印度教根本毫無關聯,皈依基督教吧!」
這些傳教士敢大放厥詞也是其來有自,過去數十年無論是英國甚至印度人類學家,如杰哈(D. N. Jha)博士都曾寫道:「第一批雅利安人的膚色多為明亮,而印度原住民的膚色要暗沉許多;皮膚顏色對他們來說應該是重要的身分象徵。」可惜杰哈博士與其同行都錯了,近期許多遺傳研究由知名人類學家主持,其中包括知名人類學家瓦林柏(S. R. Walimbe);瓦林柏曾研究摩亨佐-達羅出土的骸骨,與意外發現出土的不同時期骸骨相比後,得出了以下結論:哈拉帕人和今天在此區繁衍的印度人,有著延續的基因。
自一九九○年代起,在西方已經過驗證的群體遺傳學被應用在南亞族群上,尤其是假設的「雅利安人侵略」。遺傳學家從哈拉帕出土的骸骨中,分離出Y染色體(只能由父傳子),並與現代印度人(居住於古哈拉帕地區和印度其他各地區)的Y染色體相比,得出的結論十分具有說服力;在這個基礎上,遺傳學家帕爾塔.瑪祖達爾(Partha Majumder)表示:「無論各區之間的語言或文化差異性有多大,我們在印度所有地區都找到一組明確的哈拉帕X染色體證據(雌性染色體)。」另一位遺傳學家圖瑪斯.奇維席爾德(Toomas Kivisild)從一九九九年起便主導一系列對於所有南亞族群的研究,範圍自緬甸起至阿富汗。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對於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假設就算真實存在過,也並未對印度的基因庫造成重大影響;印度人身上所顯現出高加索人種的特徵,可被視為前高加索人的表現,這種特徵表現來自於非洲北部和東北部的基因庫。」
人類學家蘇珊塔.羅伊舒德赫利(Susanta Roychoudhury)和同事在二○○○年對六組不同族的印度人展開基因測驗,測驗結果發現「有一組基本基因單位連結起這六組人」。這些研究員也發現了單倍群U」,它常見於北印度人及高加索人種基因中;這也表示有一群人在父系或母系方曾有同樣的祖先,而現今仍存在於印度東部的部落中,如羅德哈(Lodha)或桑塔爾(Santal)。早期護航雅利安侵略論的人,經常用單倍群M來辯駁,而科學家對多數單倍群M的分析,證實了「在印度六○%的人口身上有單倍群M,其中包括部落和下層種姓人口,而且不分地區。」因此,「由於雅利安人入侵而造成高低種姓階層明顯的分別」這樣過於簡單的推論,被上述結論完全粉碎了。奇維席爾德與同事的確也發現了「高種姓與部落、下層種姓人口,共享超過八○%的連鎖基因」。
還有第二項研究,以檢測Y染色體單倍群M17,專注於研究早期印度人的遺傳基因;這被認為是雅利安人種的基因特徵。奇維席爾德在印度南部的兩支部落中發現這種染色體,其中一支部落是楚朱人(Chenchus),他們被發現在基因上與幾個高種姓階層十分接近。研究人員對此下的結論是:「印度高層種姓人口和部落民族的基因之間,沒有驚人的差異」。遺傳學家昂德希爾(Underhill)在二○一○年主導的研究,針對了同屬單倍群RLA的南亞人口之Y染色體關係,他也假設這種單倍群僅存於印歐人種。研究結果與之前得出的結論皆同。
講到這裡就一定得提到「阿迪瓦西」(Adivasis),在印度將表列部落稱為阿迪瓦西,而許多歷史學家則視阿迪瓦西為印度的原住民。人類學家經常大膽假設今日的部落民族,是由印度原住民後裔所組成的。這個概念源自於十九世紀的人類學,並為印度人對社會、政治與經濟的思考模式塑形;無論是在印度北部與南部、梵語和坦米爾語(tamoul),或是婆羅門和賤民之間,至今仍有潛在的衝突。印度女人對於擁有白皙皮膚更是有著狂熱的執著,上百萬的印度女人會買不太昂貴的乳霜,只求能夠讓皮膚變白。然而,在所有印度偉大的古籍中(例如,可與荷馬所著《伊利亞德》﹝Iliade﹞和《奧德賽》(Odyssée)媲美的史詩《摩訶婆羅多》),我們可以窺見印度古老傳統,而典籍文中並未特別區分當時的部落和其他種姓人口。現代人類學家米歇勒.波凡(Michel Boivin)也記下:「首先,很多古代部落會在社會階級上攀升,而成為剎帝利等貴族」。
另外,對於阿迪瓦西(印度原住民與賤民)的基因研究也顯示,阿迪瓦西也擁有與印度其他種姓相似的Y染色體,而北印度與南印度的高層種姓人口,在基因譜上無特別連結,但南部種姓與南部部落人口的Y染色體卻十分相近。這又再一次令人質疑,阿迪瓦西與低層種姓是印度原住民後裔的推論。此外,還有一項更新的研究,瑞迪(M. Reddy)在二○一四年指出:「我們在印度種姓人口和部落人口身上,並未發現重大的DNA差異。」
支持雅利安人侵略論的一項重要基礎,是今天所有達羅毗荼語系(坦米爾語、康納達語﹝kannada﹞、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泰盧固語﹝telugu﹞)的人,都是印度原住民的後裔;而這些原住民是在印度雅利安人入侵之後,從印度北部逃至南部定居,這又回到哈拉帕人屬於達羅毗荼語系的說法。然而,幾乎沒有遺傳研究可以證實這項推論,遺傳學家諾亞.羅森伯格(Noah A. Rosenberg)把幾組屬於印歐語系的人和達羅毗荼語系的人相比較後,也如此認為。遺傳學家桑格哈米特拉.桑格普塔(Sanghamitra Sengupta)在研究過三十六組種姓和印度群組後,證實早在所謂的「雅利安人入侵」時期前,印度次大陸的基因型態就已經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