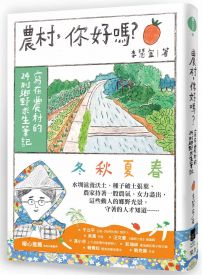【第一部・春】
春,不只是開始
西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島,緊緊偎著東亞大陸的東南側,恰恰被北回歸線輕輕滑過。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七成是山地和丘陵,超過九成的人,住在西半邊,絕大多數的資源供應歸線以北,島的西北邊明顯過重。
很少有人注意到,歸線以南的世界,有什麼特別。少有的南北向大河?檳榔樹遍布的田野風情?南方特有的落山風?哈哈!還有,紅燈不一定要停和騎車免戴安全帽的全民共識。其實,光是季節演變的風景,就夠讓人大開眼界的了,像是冬日如春,而春天,既是結速束也是開場白。
除了高雄市、台南市和屏東市,南島上放眼一望,盡是農村。位於荖濃溪、旗山溪出山口匯流處的美濃,是其中代表。
每年農曆年前,農人忙著春耕,等到第一期春耕結束,不得不服老的老農,通常會在第二期選擇休耕,讓田、讓人都喘口氣,也讓夏颱致災程度降到最低。中秋節前後,第三期的冬季裡作開始,也到了一年之中最忙碌的階段。紅豆、黃豆、玉米、長豇豆、四季豆,大瓜、南瓜、冬瓜、地瓜和白玉蘿蔔,茄子、辣椒、小番茄,和即將走入歷史的菸葉,各種作物在農民雙手指揮下,譜出熱鬧活潑的田園樂曲。
第三期裡作的一切歸功於南島的冬天:少雨、氣候溫和。冬天在這兒,一點兒都不冷,比春天還春天。
真正的春天,反而是一年的尾聲。紅豆、白玉蘿蔔、玉米、和部分瓜類都已收成,豆科作物和各種茄科,也即將劃下句號。春節前,各行各業大啖尾牙,美濃的農民,也不落人後。除了各產銷班的聚餐之外,民國一百年起,一到立春農民節,農會會在掌管農業的五穀廟前,大張旗鼓擺出一百五十桌的流水宴席,犒賞辛苦一年的農民。現場擠了兩千多人,光是台上的頒獎、抽獎,就可以從六點延續到九點。
這是一年裡,農民最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象徵一年的勞動,終於結束,來年就要展開。無論之前賺錢、賠錢,還是只有領到政府的災害補助,舊的讓它過去,新的才會來。
在美濃,春天是一連串緩慢的長鏡頭組成的蒙太奇電影。風輕輕吹起水田的漣漪,水圳蜿蜒流轉踩著小碎步唱歌,原野上的奇花異草紛紛伸長脖子只為親嚐晨光下的第一滴露水。
晨意微寒、日頭溫暖。田裡水光粼粼,新秧種在朵朵浮雲上。
〔節氣〕穀雨
第六章 樹命
高雄旗山、美濃和屏東里港交界的台糖地上,是台灣目前最廣大的外銷毛豆種植區。過了清明後,毛豆開始收成。大白天的,收割機轟隆隆在平原上漫步,有的時候,成熟期比較集中,深夜也得趕工採收。
二〇一四年以來的這三年,我年年都曾在夜裡與割豆機相遇。看著遠方黑暗無邊的毛豆田,有兩、三個亮點直線前進,靠近一些,還能看到一莢一莢的毛豆,快速的被割豆機吞進肚子裡。空氣中,混雜著白天炙熱陽光和涼夜下毛豆梗傷口的新鮮味道。
一次,老大樂樂跟著我在國道十號上披星戴月,一下高速公路轉進台三線,在回美濃的路上,先是聞到遠處飄來的陣陣青草味,接著又馬上聽到割豆機的吼聲。在車上睡著的樂樂,被我興奮地叫醒,「樂樂、樂樂,趕快起來。你看那裡,有大車子耶!」
樂樂揉了揉眼睛,口齒不清噥噥道:「媽媽,那是在割豆仔啦!」
我提高音量:「你看那裡,有沒有?割豆機一直開過來耶!」
樂樂的睡意漸消,一邊伸懶腰一邊問:「媽媽,回到家了嗎?」
我心裡為之一振。沒錯!聞到收成的味道,就知道家不遠了。
1 雨來了
已是穀雨。
往年此時,雨量漸漸增多,不過二〇一六年這一年,穀雨節氣未到,全島已經下了好幾場大雨,說是滯留鋒面的關係。小時候曾聽媽媽說,「入夏前,只要每下一場雨,氣溫就會一次比一次高。」
美濃的四季中,就屬夏天是最難熬的季節。平時炙熱難耐,一旦颱風襲來,或颱風過後旺盛的西南氣流,市區難逃淹水的命運。我有一位將近七十歲的舅舅,從小雙眼失明,但是膽子很大、人很機靈,他年輕時環島流浪,以算命為業。一得知我婚後會定居美濃,他第一句就是:「个所在到熱天,一定會發大水。」(那個地方只要到夏天,一定會淹水。)
我想起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七日。那天,是我第二次在美濃採訪淹水災情。
這一天的下午三點,卡玫基颱風開始在美濃降下大雨,連續五小時,雨勢不但沒有趨緩,到了晚上八點,還越來越強勁。馬路變成河道,垃圾在水裡載浮載沉,蟑螂、蜥蜴忙著踩水逃命,還有一張書桌也漂在水面,美濃溪溪水已經跟橋面一般高,消防隊員在路口拉起封鎖線
瞬間,大水漫上街道,沖進民房。
美濃溪和中正湖排水流經聚落,在天后宮前又與竹仔門排水匯流,三條水路在此相遇,這處地名被稱為三浹水,只要淹水,就屬這一帶最為嚴重。聚落內是南北向的中正路為縱軸,北以泰安路為界,南到成功路,這一帶是美濃最熱鬧的區域,包含各公務機關、水電瓦斯郵政機構,還有農民最常進出的農會大樓、傳統市場,全都在淹水範圍內。
美濃人個個被淹水訓練成精。無論一般家庭還是商家,大家在這幾年,都已經陸續備妥擋水鐵板和抽水機。可是美濃人還是很難想像,為什麼美濃溪會變成如此可怕的惡水?
卡玫基颱風在半天時間,累積三百多毫米的雨量,使得鬧區成為水鄉澤國。住在永安路上的林英清,曾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理事長,他們家世居聚落裡的最低窪處。民國六十六年到現在,林家夥房歷經三次整建,每次都把房子墊高,但還是逃不過被水追著跑而最終被水淹的命運。看著水在客廳、房間留下的淤泥黃沙,林英清指著東北方的遠處說:「淹水的關鍵原因之一,就在那片山林裡!」
美濃溪的上游雙溪,也稱為黃蝶翠谷,曾是引爆反水庫運動的美濃水庫預定地。每年四、五月起,會有成千上萬的黃蝶在此棲息。這片森林,過去在坡地上有農業開墾,現在底部鋪滿水泥,是典型的三面光 河川整治工法,近年山坡兩側流失的土泥,剛好順著水泥河床往下奔流。
好幾次颱風期間,我趁著地利之便搶先趕到民宅採訪,外出工作的年輕人大多還沒回到老家,我總是看到獨居在家的老先生或老太太,拄著拐杖站在門口發呆,口中喃喃:「仰結煞啊!仰結煞啊!」(怎麼辦啊?怎麼辦啊?)
一身狼狽的受災民眾,只要看到攝影機,第一個反應就是破口大罵,「短命鬼!仰會恁短命!一定係雙溪个樹仔分人斲淨,樣會淹水淹到恁嚴重。汝看看,這恁汶个水,分明就係仞崗無樹嘞啊!」(短命鬼!怎麼這麼夭壽!一定是雙溪的樹被砍光了,才會淹水淹得這麼嚴重。妳看看,這麼混濁的水,分明就是山上沒有樹了!)
2 源頭、元兇、園地
黃蝶翠谷在地的農民,人人都知道雙溪集水區土質鬆軟,再加上八八風災造成高屏溪流域嚴重的山林崩塌現象,也包含支流美濃溪的上游雙溪。民眾需要的,是政府舒緩或降低崩塌帶來的衝擊,可是相關單位的做法,卻常常反其道而行。
二〇一一年年中,林務局表示為了整治雙溪山坡地,在「一百年度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中編列一千二百萬預算,計畫發包「水底坪坑溝治理一期工程」以及「冷窟崩塌地處理工程」。消息一傳出來,美濃有將近二十個民間社團,集體要求林務局暫緩執行。
六月初,林務局到美濃舉辦工程計畫說明會。會議上,美濃環保聯盟的林俊清說:「水災和地震這些天然災害,對台灣山林造成很大的破壞,像是美濃的雙溪流域,根本不適合再進行任何工程。」
美濃愛鄉協進會邱靜慧也表示:「雙溪集水區應以『滯洪』而非『排洪』治理,如果把大石頭移開河床,上游的水流,反而會像拉肚子一樣直洩而下,很有可能讓聚落淹水的情況更嚴重。」
林俊清進一步說明這些年觀察的經驗。他強調:「雙溪上游崩坍的主因,除了天災之外,果園種植、開筍路挖竹筍,使得山坡地林相不是過於單一就是遭受破壞,這些也都是水土流失崩坍的元凶。林務局如果還在這個緊要關頭,移除河道裡的大石頭,那只會讓大水加劇沖蝕基準面。現在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研擬退租還林政策,讓黃蝶翠谷可以真正好好休息,恢復集水區的滯洪功能。」
每年七月,整個美濃幾乎都沉浸在黃蝶祭的氣氛裡。祭典上,主祭團參拜黃蝶伯公,請土地神護佑黃蝶翠谷,期待人類不要再過度開發破壞生態。可是二〇〇七年黃蝶祭後的第二天,七月二十四日,在黃蝶翠谷的雙溪母樹園裡,卻上演著一場角力戰。
到底雙溪母樹園的入口,該不該興建木棧道和平台呢?當時八色鳥協會理事長黃淑玫與林務局委託的景觀規劃設計師呂兆良,兩個人爭得臉紅耳赤。政府部門認為,母樹園入口附近,土壤大量流失、樹根嚴重裸露,所以必須興建平台,阻隔遊客踐踏樹木生長區,才能真正保護樹林。保育團體意見完全相反,黃淑玫強調:「林務局的施工,是將樹根直接砍斷,然後灌水泥、架平台,這只會讓母樹園的老樹加速死亡。」
美濃國中老師劉昭能也一直關心這個議題。他說:「日本政府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在美濃建立一個樹木園,樹木都是從熱帶地區,像是南洋、中南半島、大洋洲、南美洲,甚至非洲等地移植到台灣來,一共有二百七十多種。如果這些樹木生長情況良好,日本政府就會將台灣作為造林、選種的基地。」
老師口中的故事,現在已成大樹。中南半島的大風子,印度、馬來西亞的鐵刀木,還有大洋洲的太平洋鐵木,都紛紛漂洋過海來到台灣落地生根。這些外來的熱帶樹木,現在還有九十六種。
八十多年的母樹園內,隨處可見高聳入天的熱帶樹種,森林裡的高處,有綿密交錯的樹冠層,低處有雙溪圳的源頭川流而過,還有靜悄悄長在石頭上的蕨類或苔蘚。到了五月黃蝶大發生時,為了啄食蝴蝶,八色鳥、五色鳥、紅嘴黑鵯、綠繡眼、藍磯鶇等鳥類,會集中棲息在園區內,形成愛鳥者的朝聖地。這片自成一格的雨林,是日本人在美濃留下的歷史軌跡,也是外來種植物在台灣被自然環境馴化後的見證。
3 一樹一神
在美濃,舉目可見芒果樹、苦楝樹、樟樹、榕樹、龍眼樹、茄苳樹。無論是老樹、巨木、樹群、森林,很多樹早在人們開墾前,就已經落腳在這片土地上。
我們家荔枝園旁,有一條淺淺的小溪——旱溪,夏天才有水流,冬天時是伏流水 ,乾涸的溪底會傳出陣陣水流聲。這看似平凡的溪畔,有幾排長滿青苔據說是早期祖先開發時所留下的石駁 。一棵老龍眼樹,就長在石駁旁的土堆上,部分根系還爬進石駁的空隙,把圓鼓鼓互相卡得緊緊的石頭,又抱得更密實了。
這棵老龍眼樹,沒有人知道祂年紀多大,但家族的每個人都尊敬祂、信仰祂,當祂是聚落與家族的守護者,為祂興建一小座土地公廟,讓有需要的人,可以走到樹下進入廟裡跟祂說說心裡的話。
第一次陪阿姆去祭拜這棵樹前的旱溪伯公 ,是二〇〇九年婚後沒多久。當時,我大開眼界。
平日靦腆但說話大嗓門的阿姆,雙手合十緊夾三支香,壓低音量口中唸唸有詞:「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