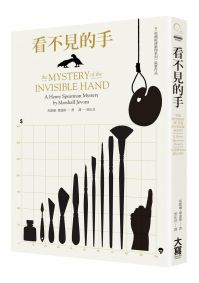1.史匹曼拜見國王
十二月十日/週五晚上。
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的想法,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常人以為的還更要強大。的確,世界是由其他的少數人所把持。認為自己能不被任何智識影響的平凡人,通常都是某些廢經濟學家的奴隸。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在這個特別冷的十二月夜晚,史匹曼正是「人要衣裝」的最佳範例,或者以他自己來看,是剛好相反。大禮服後面的衣角距離地只有幾英吋,非但沒有拉長他的身形,反而看著更顯圓胖。但他倒是不擔心衣服,要煩惱的是等會兒上場的禮節。今晚,他要拜見國王。
地點是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的「藍廳」(Bla Hallen),史匹曼前來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天已經非常值得紀念了:遊覽歷史地標和瑞典建築,接著是晚上的諾貝爾晚宴。65張桌子,坐滿瑞典王室家族、得獎者、特別來賓與其他客人。桌巾是超過三百年的皇室御用品牌「艾克倫」(Ekelund),桌上的「羅斯蘭」(Rorstrand)瓷器與「歐瑞佛」(Orrefors)水晶杯映著昏黃的燈光閃閃發亮。餐點是瑞典式美食,有鮭魚、龍蝦,還有野味。餐桌上的談話五花八門,娛樂更是頂級。最後來到典禮的時間,史匹曼在心裡默默算著等等要自己要做的禮節。雖然之前也曾受過獎,但這次可是學術界的最高榮譽。就連名字「諾貝爾」,感覺都更為更光榮。要是換成像「瓊斯獎」,可就沒這麼威了。
不過這個諾貝爾獎來得也不是那麼意外。年過五十的史匹曼是舉世聞名的作者,也引領著重大思潮。還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時,老師便看出他的優異。到了研究所期間,教授群也一致認同他是明日之星。來自哈佛大學經濟系的邀請,更顯示學術界所見略同。他也沒讓人失望。史匹曼很快就讓這間大名鼎鼎的系所更添光彩。
當史匹曼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一出,哈佛的公關部門立刻大肆宣傳。有些學校是在美式足球場上廝殺,但哈佛與長春藤名校則是在教授贏得的學術獎項上比拼。贏得大學賽獎盃可以讓學校登上報紙的體育版。但諾貝爾獎可是頭版頭條等級的榮耀。在經濟學領域,芝加哥大學是諾貝爾獎得主的搖籃,數量遠勝其他任何學校。史匹曼獲獎,會讓哈佛在芝加哥的地盤搶下一席。
在典禮上,史匹曼的太太佩吉一身明豔動人的淺藍亞麻禮服,襯托出豐滿的體態。在佩吉旁邊坐著兩人的女兒派翠西亞。這禮拜她放下獸醫工作,專程來斯德哥爾摩見證典禮。「動物得先等等。」她笑著說。
當主持人說出,請經濟學獎得主「上前從國王陛下手中接過諾貝爾獎」時,史匹曼站起身,走到舞台中央,和皇室握手,然後鞠躬,一如受獎指示。這輩子第一次,有皇家管弦樂團的喇叭齊鳴,慶祝他作為經濟學家的成就。同時這也是這輩子頭一遭,史匹曼一舉進帳一百萬元。
在返回波士頓洛根機場的飛機上,史匹曼回想自己的根源。他的父母在希特勒稱霸之前來到美國,幾乎身無分文。史匹曼從小在父親位於布魯克林的裁縫店樓上長大,在人生前二十年,那就是他的世界。現在他回到當年雙親逃離的大陸,接受皇室款待。更重要的是,從此之後,他將和眾多經濟學巨匠齊名,包括:
艾克羅夫Akerlof
艾羅Arrow
貝克Becker
布克曼Buchanan
寇斯Coase
傅利曼Friedman
海耶克Hayek
康納曼Kahneman
盧卡斯Lucas
納許Nash
舒茲Schultz
森Sen
史密斯Smith
梭羅Solow
史蒂格勒Stigler
史迪格里茲Stiglitz
托賓Tobin
維克律Vickrey……等等
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從此不再相同。
結果也的確不同。
3.寇斯不擔心
十一月十五日/週二下午
「這又是你另一個怪主意,」局長說,他習慣把任何自己無法理解的事情冠上「怪」之名,因此活在一個絕對「怪」的世界。
──小說家 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布雷克‧貝禮瞄了一眼大廳,看到史匹曼教授走下走廊,趕忙走到他面前。貝禮長長的紅髮從波士頓紅襪隊棒球帽伸出來,臉上的黑角眼鏡讓他的髮色越發明顯。當貝禮上氣不接下氣追上史匹曼時,這位名經濟學家正和同事談得口沫橫飛。這是中午時分的哈佛樓,主要的教室大樓。多數時候這棟樓的大廳和樓梯都是空盪盪的。但今天這個時候,又餓又吵剛下課的學生,從各個教室門口魚貫走出。
「史匹曼教授,不好意思打擾了,但我得請教你一件事。」
「喔?」史匹曼教授皺起眉頭看向貝禮,認出這個無理的提問者是剛下課的中間產品價格理論課學生。他心裡暗暗笑了一下。布雷克這種學生在每個課堂每個主題上都看得到,上課時安安靜靜,總等到鐘響後才大鳴大放。
貝禮還沒提出問題,史匹曼就舉起手,指著他的同事說:「貝禮先生,你認識心理系的韓德森‧羅斯博士嗎?」
25年前,史匹曼和羅斯都從哈佛開始學術生涯。即便兩人研究天差地別,但還是結成了好友。羅斯高頭大馬一頭黑髮,史匹曼則是禿頭矮個兒。羅斯戴隱形眼鏡,史匹曼則喜歡眼鏡。羅斯穿得像嬉皮,總是一身牛仔褲和圓領衫,再背個帆布書包。要是不看年紀,或許會以為他是40年前從校園示威抗議裡直接過來的。另一方面,史匹曼則是落伍20年的風格。高中生樣的卡其褲、襯衫和條紋領帶和獵裝外套,拎著裝滿上課講義的公事包。讓兩位教授結成好友的,是他們拿到哈佛終生教職的生存記。撐過死亡之路的少數幾位士兵總會很快成為好友,不管種族、膚色和信仰。能夠拿到菁英大學終生教職的少數教授也有著同樣的惺惺相惜。
「嘿,你好嗎?」貝禮回話,在史匹曼介紹完後,看了羅斯一眼。
「不錯,你好嗎?」
「呃,應該還過得去」在轉向史匹曼的那一瞬間,貝禮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當一位心理學家問:「你好嗎?」有什麼弦外之音?是不是個深層複雜的問題?但年輕大學生知道要是追問羅斯的真正意思,會岔開他要請教史匹曼的問題。
「史匹曼教授,我不太懂你上禮拜的課,關於房地產開發商的?你最後說即便一個人擁有全美國的土地,也無法用獨佔價格價。對嗎?」
講到這裡,羅斯一臉同情這位好奇的年輕人。心理學大師拍了拍年輕人的背,對他的同事笑著說:「老史,幫這個可憐的孩子一把,讓他搞清楚這件事。顯然他聽錯了,我一直說你收太多學生了;結果就是這樣。我們知道從心理學上來說,小班教學激勵效果比較好。」
史匹曼笑了笑說:「雖然教室裡人很多,但貝禮先生的聽力沒問題。我就‧是‧這樣講的。要是你擁有所有的土地,你會和洛克斐勒一樣富有。這點無庸置疑。但你無法以獨佔價格標記任何一塊土地。」」
「拜托,老史,聽起來是狡辯。」
「不、不」史匹曼回答:「讓我稍微換個方式說,請問兩位,假設某人擁有全美國的土地,假設你想跟他買個幾畝地當成投資,要是他不保證不用更低的價格出售那塊地的額外部份,你還會買嗎?」
「當然不買。」史匹曼自問自答,解釋說:「否則你要怎麼保護自己的投資?至少你會堅持,要是他要以更低價格出售更多土地,賣方得用你支付的價格買回。或是你會堅持他拿出的任何其他土地,會用於像是公園這種非商業用途,不會影響你的投資。否則,」他停了一下,確認兩人都還專心聽他講:「你或是任何其他理性的經濟人,永遠不會買任何地。所以,貝禮先生,就像我在課堂上講的,即便是擁有所有土地的人也要受市場所規範。名叫寇斯(Coase)的經濟學家首次提出這個論點。現在我們稱之為寇斯猜想。」
史匹曼熱切地想從聽者臉上看到初次領悟的表情,但並沒有發生。他把手放在學生肩上,繼續說:「貝禮,我在課堂上的論點是這樣。假設你賣某樣耐久財,某種不會因為時間或要素而改變的東西。而你面對的買方可以延後採購,那麼時間本身會變成替代品——就像有個看不見競爭對手在壓低耐久財的價格。所以即便你是唯一銷售某樣耐久財的人,要是你不能讓人相信未來不會調整價格,你將無法行使獨佔權。」
史匹曼等著對方回應,但沒反應。心理學家看著貝禮說:「年輕人,你看,史匹曼教授就是有這本事,讓我們聽得一愣一愣,就是這樣他才這麼受學生歡迎,讓我們其他教授眼紅。有時候我們有些人甚至懷疑,史匹曼可能是對的,或者他只是講得似是而非。」
面對羅斯善意的揶揄,史匹曼只是一笑置之。他知道他們兩個人對世界有不同的觀點。但史匹曼永遠樂觀地認為,在意見的領域裡,經濟學的思維最終會稱霸。至於羅斯這邊則擔心,即便史匹曼的經濟學是錯的,但他說的可能正確。
史匹曼從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和獎金回來之後,羅斯也開始更仔細觀察這位朋友。身為心理學家,羅斯知道佛洛伊德從來沒有分析過「同儕嫉妒」。佛洛伊德的嫉妒理論是以別的主題為中心,是人心下方的那個部分。但是非常熱中於觀察大學生活的羅斯認為,「同儕嫉妒」或許是學術成就的可靠指標。而且他也知道,現在好友史匹曼正是活生生的例子。
兩位教授和學生閒聊在愉快氣氛下的結束,大家各自離開。沒課的時候,在哈佛教職員俱樂部裡,大家都知道史匹曼很健談,也喜歡和他一塊用餐。但在結束早上的課之後,他會回到立陶爾中心的辦公室裡獨自用餐。他發現上課很累人,特別是課程進行順利的時候。教好一堂課原比敷衍了事要費力得多。
史匹曼在上完課後不想和人打交道還有另一個原因。這些年來他瞭解到,評估上課進展狀況的最佳時機,就是在剛上完課之後。史匹曼認為,等上好幾個月甚至是一年才重新檢視教材的人,是錯誤的。等到那時,哪裡做對哪裡做錯,早就忘記了。
羅斯知道史匹曼一心想要教得更好,也曾一度問他:「老史,在你教完做課後評估的時候,怎麼樣才能被你認為是完全滿意,無法再更好?」史匹曼笑著,眼睛閃呀閃地說:「好的課,不需要再改進的課,是當學生把你扛在肩上走出教室,遊行繞校園一週的時候。羅斯也回答得一本正經:「照這樣來看,我們多數人一年只有教出幾堂好課而已。」
吃著輕食,史匹曼拿起桌上的《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因為他是個經濟學家,學生總期待他能飽覽世事,即便學生自己做不到。在報紙的第二落,有一則標題抓住了他的目光:
〈德州藝術犯罪〉德州聖安東尼奧(美聯社電):
州警與地方警察於11月14日搜索聖安東尼奧知名外科醫生兼藝術收藏家勞爾‧拉莫司醫生的家,調查他家被闖入的事件。他所收藏的本地著名藝術家崔斯坦‧惠勒的五幅畫作也因此失竊。
被偷的畫作包括惠勒的〈藍色畫像〉(A Portrait in Blue),根據畫家所言,這幅畫代表他「終於能突破現代藝術的資本家侷限」,也是他在國內成名的一連串畫作的第一幅。
警方在中部標準時間凌晨三點接到來自歐克蒙大道住宅的報警電話。家裡的女傭被起居室的聲音吵醒,而畫作就放在起居室裡。搜索家裡的警方並未對記者評論案件細節。
拉莫司是聖安東尼奧藝術界裡的知名收藏家,也經常主辦慈善晚會支持城裡的藝術博物館。聖安東尼奧崔維斯美術館的路易斯‧馬丁告訴記者,某位晚會的貴賓可能聘請專業竊賊下手。拉莫司聽到這個說法時,也承認有其可能,表示他想畫作可能不會被尋獲。「我不覺得我可以找到這些畫。最後大概會落入某人的私人收藏,其他人都再也不會看到。」拉莫司醫生說,他損失甚鉅,因為這些作品都沒有保險。他也拿出一百萬獎金想要找回畫作。
多數專家相信,在這樣的案子是在跟時間賽跑。「藝術竊案必需要能快速破案。一旦藝術品消失一陣子,通常就永遠也找不到了。」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警衛長席尼‧范‧佩特(Sidnee Van Pelt)是藝術竊案的專家。他向《波士頓環球報》做出如上評論。
史匹曼按下電話上的對講按鈕,呼叫他的長年助理葛洛莉亞‧溫特斯。當她進到辦公室時,史匹曼把報紙拿給她,指著他剛才讀到的報導說:「葛洛莉亞,麻煩把這則新聞剪報存檔?」
「你想要存在哪裡?」溫特斯問。
史匹曼摸著下巴,瞇起眼睛想了一會兒。「放在我們要送到聖安東尼奧的箱子裡。然後標上『吠叫的狗』檔案夾」。
4. 偵訊竊賊
十一月十五日/週二下午
把每件事都倒過來看。絕對不當成是理所當然。
──迪克•法蘭西斯(DICK FRANCIS)
「讓我搞清楚,你是有聽到還是沒有聽到樓上有人?我不懂是哪個。」費茲‧席格菲警探正在聖安東尼奧警局偵訊蘿西‧瑟古拉。他一屁股坐進辦公椅,聲勢驚人。當他舉起手臂把手肘放在桌子上時,這位魁武大漢的二頭肌漲得跟葡萄柚一樣大。他懷疑地打量著小女傭。他的手下一開始抵達拉莫司家裡調查竊案時,已經偵訊過她了。席格菲知道在聖安東尼奧的多數拉丁美洲裔人士都是守法的公民。
但是蘿西的說法裡有幾個矛盾之處,他決定要自己問清楚。「我說我有聽到,但然後我又沒聽到,然後我又聽到了。等我又聽到的時候,我就走上樓梯,帶著我的剪刀,去看看我聽到什麼。」蘿西用哀求的眼神看著席格菲。她一點也不怕被驅逐出境,但她得有個好工作才能寄錢回去墨西哥給靠她生活的家人。當政客爭論移民議題時,對她來說關係的不是公共政策,而是經濟存亡。
「你說你上樓去的時候,有看到人嗎?像是你說你聽到的人?」
「沒有,我沒看到人。」
「你上樓時是幾點?」這問題已經有人問過了,但席格菲不罷休。因為罪犯常常說謊掩蓋自己的舉止,故事裡的矛盾常會透露出更多內情。
「我講過了,那是凌晨兩點半。我床邊有個鐘,我聽到噪音起床時看了時間。」
「所以你聽到噪音,有人在樓上,但你說不出是誰。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說不出是誰是因為我沒看到任何人。我上樓的時候,樓上沒有人,至少餐廳和客廳裡沒有。然後廚房也沒有,走上樓會先到廚房。」
「你有查看櫃子嗎?還是只有餐廳跟客廳?」
「我才不敢看櫃子裡。我上樓之後,拿了一把菜刀,但我還是不敢看有沒有人在櫃子裡。等我查過飯廳和客廳時,我就叫拉莫司先生,然後他打給警察。」
「瑟古拉女士,」警探一改嚴厲的語氣,用一派慈祥爺爺的口吻說:「如果你沒看到人,又怎麼知道有人來過?」
「因為畫作全部都不見了。所以我知道。」蘿西看警探的眼神,好像他是個無聊的孩子。「我昨天跟警察說過了。我知道畫作不會自己長腳跑到屋外。一定有人在樓上。不管是誰,那就是我聽到的人。」
「如果畫作不會自己出走,那麼就是有人拿走了。可能是你的老闆,但你說你叫他的時候他在床上,對嗎?」
「對,他在他的臥房裡。」
「你說你在拉莫司醫生這裡工作多久了?」
「快要七年了」蘿西說,不懂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不是你老闆拿走畫,我猜可能是你拿的。你知道畫在那裡。你也在這裡工作夠久了,對房子裡的每個角落縫隙都瞭如指掌。屋子裡大概有你知道但拉莫司先生不知道的地方。」
當席格菲警探說她可能是賊的時候,蘿西明顯震了一下。「不是,不是,你不明白。我關心拉莫司醫生。我工作很認真。我永遠不會偷拉莫司醫生的東西。這些年來我一毛錢都沒偷過,你覺得現在我還會偷他的畫?」蘿西又露出求情的眼神。
「但如果不是你做的,拉莫司醫生也沒有偷他自己的畫,又怎麼會有別人偷?你的老闆說他起來的時候門是鎖著的。我的人也沒發現窗戶被打破或撬開的證據。那天晚上還有別人在屋子裡嗎?有家人?」
「只有我們。我老闆他離婚了。他有兩個小孩,但是都長大了。兒子住在奧斯丁,女兒住在北邊,密爾瓦基,我最近聽到拉莫司醫生說。」
席格菲警探躺回椅子上沈思。如果蘿西想要偷老闆的東西,為什麼要偷藝術作品?身為女傭,她不太可能知道要怎麼把高價的畫作銷贓。而且,為何要叫醒老闆?除非這本身就是要擺脫警察的計畫…?另一方面,在警探的工作裡永遠有另一方面,席格菲知道某些罪犯之所以得手,就因為罪行看起來太不可能。
蘿西有可能等待時機下手,避開偷老闆零用錢這種比較明顯的誘惑,轉而朝大筆的下手:房子裡最值錢的資產。此外,拉莫司醫生經常在家招待客人,而拉莫司家裡的社交活動也和藝術社群有關。蘿西可能會聯繫其他人,或是有人找上她,藉由她來把畫作移出房子,然後賣出變現。席格菲設想,有什麼情況會讓蘿西家裡需要一大筆錢,或許是要看病?如果是,幫忙行竊的慾望可能會壓過對老闆的忠誠。
還需要再觀察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