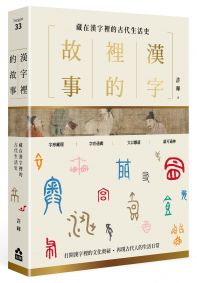炙 在火上烤一塊肉
「炙」這個字牽涉中國古代各種燒烤肉食的方法。
炙,小篆字形,這是一個會意字,意思簡單明瞭,就是一塊肉放在火上烤。《說文解字》中收錄了一個古文字形,上面肉的形狀更加明顯。
《說文解字》:「炙,炮肉也,從肉在火上。」古時帶毛的肉在火上燒,或者用泥裹起來燒,稱為炮(ㄆㄠˊ);將去毛的肉直接放在火上猛烤,稱為燔(ㄈㄢˊ);將去毛的肉在火上熏烤,稱為炙(ㄓˋ)。《詩經.瓠葉》中的這段描述很傳神:「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對待兔子頭這道美味,先塗泥裹燒去毛,然後在火上猛烤,最後再在火上慢慢熏烤。由此,「炙」也可以引申為名詞,意思是烤熟的肉食。比如李白有詩
曰:「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將烤熟的肉給朱亥吃,舉起酒杯向侯嬴勸酒。
孟子說過一段話:「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意思是:百代之前奮發有為,百代之後聽說的人沒有不振作奮發的。不是聖人,能像這樣嗎?更何況親身受到他們薰陶的人呢?南宋學者朱熹解釋了「親炙」一詞:「親近而熏炙之也。」我直接在您面前被您燒烤,
比喻直接接受別人或老師的教誨或傳授。「炙」的這個意思還體現在成語「炙手可熱」中,唐代杜甫有詩曰:「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剛剛接近就感覺燙手,比喻權勢者氣焰之盛。剛剛烤熟的肉很熱,因此「炙」又引申出在太陽底下曝曬的意思。三國時代嵇康所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有一句話:「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意思是鄉野之人曬太陽取暖,以陽光曝曬背部為快事,又以隨處可見的水芹為美味,於是想將這兩樣東西獻給皇帝,表示對皇帝的效忠。如此微薄又毫不稀罕的兩樣東西,野人卻認為是世間至樂,真是可笑之極!因此嵇康感嘆說:「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最有趣的是「膾炙人口」這個成語。膾讀作ㄎㄨㄞˋ,指切細的肉或魚。《孟子.盡心下》中講了一個故事。曾子(即曾參)的父親曾皙(即孔子的學生曾點)喜歡吃羊棗。羊棗是一種黑棗,因為顏色和形狀都像羊屎,所以俗稱「羊矢棗」。曾子的父親死後,曾子從此不再吃羊棗。
孟子的學生公孫醜對曾子的這種做法很不理解,於是向老師請教說:「膾炙與羊棗孰美?」切細的肉、烤肉和羊棗相比,哪個味道更好?
孟子回答道:「這還用問嗎?當然是膾炙的味道更好了。」
公孫醜又問:「曾子的父親生前同樣也喜歡吃膾炙,如果是為了紀念父親,他乾脆連膾炙也不要吃了,為什麼偏偏不吃羊棗?」
孟子回答道:「膾炙是人人都喜歡的,羊棗卻只有曾皙一個人喜歡吃。就像避諱是避諱名而不避諱姓,姓是人人都有的,而名是一個人獨有的。」古時候,遇到和父親的「名」相同的字時,就要避諱這個字,或者刻意缺筆,或者用同音字替代,但是卻不用避諱姓,這是因為「姓」是人人都有的,而「名」則是一個人獨有的。「膾炙所同也」,膾炙就像「姓」,是人人都喜歡的;「羊棗所獨也」,羊棗就像「名」,只有曾皙一個人喜歡吃。因此,曾參就像避諱獨有的「名」一樣,避諱父親愛吃的羊棗。
聽了老師這番深入淺出的解釋,公孫醜恍然大悟,我們也恍然大悟。
孟子的原話是「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後來人們從這句話裡引申出「膾炙人口」這個成語,用來形容人人都讚美的事情或者詩文。
臭 狗聞著氣味尋蹤追跡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的這句詩是封建統治階級奴役勞動人民的典型寫照。其中最顯眼的當然是「臭」字,但是如果把「臭」理解成發臭的「臭」,這句詩就變得不符合邏輯了。
朱門是指有權有錢人家的大門,只有他們才有資格把門漆成大紅色。朱門裡面大吃大喝,吃不完的就倒在外面(不管是大街上還是下水道),結果時間長了就變臭了。作為對比,朱門的酒肉變臭了,但路邊卻赫然羅列著貧民、流民的白骨,這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啊!貧富分化,杜甫的詩於是成了典型的教科書式的榜樣。
但這樣的理解是階級分析法的一廂情願。因為就像窮人在深冬的寒夜被凍死了一樣,朱門裡面吃剩的酒肉倒了出來,難道就不會凍得一點氣味都沒有了嗎?死屍沒有臭氣,酒肉當然也就沒有臭氣。大自然的冰箱不管對「凍死骨」和「酒肉」都是一視同仁的。
這樣錯誤的理解,是由於不懂得「臭」這個字所導致的。臭,甲骨文字形,這是一個會意字,上部為「自」,是鼻子的形狀。最初沒有「鼻」這個字,古人就用「自」來指稱鼻子。直到今天,人們說到自己的時候,還總是指著自己的鼻子。「臭」的下部是一隻犬,頭朝上,腿朝左,尾巴朝下。甲骨文字形,這隻狗面朝右。明清之際的《六書通》還收錄了一個篆體字形,字形更加美麗。小篆字形,變化不大。
狗是中國古人最早馴化的動物之一,古人深深懂得狗的嗅覺特別靈敏,因此用鼻子和犬會意為「臭」字。《說文解字》:「臭,禽走臭而知其跡者,犬也。」段玉裁注:「走臭猶言逐氣。犬能行路蹤跡前犬之所至,於其氣知之也,故其字從犬自。自者,鼻也。引申假借為凡氣息芳臭之稱。」
古人云:「古者香氣穢氣皆名之臭。」《廣韻》:「凡氣之總名。」清代文字學家朱駿聲解釋道:「人通於鼻者謂之臭。臭者,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詩經.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這幾處的「臭」都作為氣味之總名解。
「臭」這個字最早應該讀作ㄒㄧㄡˋ,是動詞,意思是聞氣味,不管什麼氣味,包括香的、臭的都聞。如果作為名詞,「臭」是氣味的總名,所有的氣味—香、臭、腥、臊—全都可以叫「臭」。此之謂「凡氣之總名」。
作為佐證,《易經》中說:「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同心同德,那麼我們說出來的話,其氣味就像蘭花那樣馥郁芳香。這個「臭」哪裡還有我們今天以為的發臭的意思?簡直就是知己和戀愛男女之間的吐氣如蘭啊!因此,「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跟普通的理解大相徑庭—朱門裡的酒肉散發出綿綿不絕的香氣,朱門外的路上卻因為天寒地凍,凍死了無數的窮人,有些窮人死亡時間長了,白骨都露出來了。
家 屋子裡養了頭豬
我認為「家」這個字是「最中國」的漢字之最,因為這個字隱藏著中國文化的全部奧秘。
家,甲骨文字形,是一個會意字,上面是「宀」,下面是一頭豬(豕)。「宀」讀作ㄇㄧㄢˊ,《說文解字》:「交覆深屋也。」明末學者田藝蘅解釋道:「古者穴居野處,未有宮室,先有宀,而後有穴。宀,當象上阜高凸,其下有凹,可藏身之形,故穴字從此。室家宮寧之制,皆因之。」由此可見,「宀」是人類最早的藏身之所,「宀」裡養著一頭豬,豬是中國古人最早馴養的六種動物之一,二者組合在一起就成了「家」這個字。金文字形,則「家」的含義更加顯豁:「宀」下面有一頭頭朝下的大肥豬。金文字形,豬的樣子有些變形,以至於有人誤以為是狗,但甲骨文中豬是垂尾,狗是翹尾,以此為別。小篆字形,我們所用的「家」字就此定型。
《說文解字》:「家,居也。」《爾雅.釋宮》對「家」的方位做了更精準的描述:「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扆(ㄧˇ)是古代宮殿內門和窗之間的地方,從這個地方再往裡走就是「家」。這個描述呼應了《說文解字》關於「宀」的解釋:「交覆深屋也。」家一定是深屋,位於整個宮殿或整棟房屋的最深處,因此「有夫有婦,然後為家」。
中國傳統文化往往將家、國並舉,家、國不分,家、國一體,進而形成民族潛意識,導致個人價值的缺失。孔子在《論語.季氏》中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而「國」和「家」的區別是:「國」指王或諸侯的統治區域,「家」是卿大夫的封地食邑。
《孟子》中說得更清楚:「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家」既為卿大夫的封地,理所當然地隸屬於「國」,「家」中之人也就理所當然地隸屬於「國」。因此,孟子才會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易經》中更如此發揮:「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個人服從於國家,消融於國家,從而使得中國國家至上的價值觀迥異於西方文明中個人至上的價值觀。
「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現代概念,但中文有一個全世界獨有的稱謂,就是「家國」一詞。家就是家,國就是國,何來所謂「家國」?「家國」一詞最早出自周公之口,西周立國後,周公曾訓誡群臣:「是人斯乃讒賊媢嫉,以不利於厥家國。」孔子在《禮記.大學》中將「家國」的概念表述得更清楚:「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就是儒家著名的「修齊治平」理論,展現家和國不可分割的關係。
在皇權時代,「家國」就是「家天下」,是皇帝一人的私有財產,唐肅宗曾經對重臣郭子儀說過:「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就是赤裸裸的「家天下」的表述,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與現代公民意識背道而馳的。
乘 爬到樹上去瞭望敵情
「乘」是個非常有意思的漢字,有兩個讀音。我們先來看字形的演變。
乘,甲骨文字形,這是一個會意字,下面是枝杈伸展的「木」,上面是一個人,人爬到樹上去幹嘛呢?
甲骨文字形,上面的人好像引頸眺望的模樣,大概是在瞭望並偵察敵情。金文字形,樹木和人的樣子更加舒展。金文字形,人多了兩隻腳,意為手腳並用,艱難地爬到樹上。小篆字形,下面的「木」還是老樣子,但人的樣子不太像,倒是突出了兩隻腳。楷體字形的上下結構訛變成了「禾」,人的兩隻腳則訛變成了中間的「北」。
《說文解字》:「乘,覆也。」意思是跑到上面。段玉裁解釋說:「加其上曰乘。」這個說法不太準確,從字形即可看出,「乘」的本義是登、升,人登到樹上。甲骨文卜辭中有名為「望乘」的人名或部落名,屬於商王的部隊,應該就是偵察敵情的先頭部隊。
《詩經.七月》中有「亟其乘屋」的詩句,意思是趕緊登上屋頂去修理房屋。因為人騎馬時也要登上馬背,因此引申為騎、坐和駕馭之意,比如乘車、乘船,比如《論語》中有這樣的話:「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公孫赤到齊國去,駕馭著肥馬拉的車子,穿著輕暖的皮衣。此處的「乘肥馬」不是指騎馬,而是指駕馭馬車。戰國以前車馬相連,沒有無馬的車,也沒有無車的馬。
馬奔跑的時候會加速,因此引申出「乘勢」的意思;駕馭馬匹是借助馬匹的速度,因此又引申出利用、依仗、趁機的意思。當用作這些義項的時候,「乘」的讀音是「ㄔㄥˊ」。
古代狩獵或者作戰的車子,以四匹馬拉最為常見,「乘」的引申義是「覆」,覆在上面,駕車時要把車軛套在馬的脖子上,因此這也叫「乘」,而一車用四匹馬拉,因此四匹馬拉的車子就叫作「一乘」。所謂「萬乘」即一萬輛車,這是天子之制,因此也用「萬乘」來指代天子;「千乘」即一千輛車,這是諸侯之制;「百乘」即一百輛車,這是大夫之制。
《詩經》中就有許多吟詠車馬的詩,常常出現「四牡」(四匹公馬)、「乘馬」(四匹馬)、「乘黃」(四匹黃色馬)等詞句,日常口語中也有「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說法,「駟馬」即指四匹馬拉的車子。從這裡又把「乘」引申為量詞,以四為乘,比如「乘壺」就是四個壺,「乘矢」就是四支箭,諸如此類。
《左傳》中有一個著名的故事,秦軍準備偷襲鄭國,半路被自稱鄭國使臣的弦高攔住,弦高其實是個商人,聽說秦軍欲攻打自己的國家,便冒充使臣,「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乘韋」是四張熟牛皮,先獻上四張熟牛皮,然後再獻上十二頭牛,犒勞秦師。為什麼說「以乘韋先牛十二」呢?這是因為獻人禮物時,一定要先輕後重,先薄禮後重禮。秦軍以為鄭國早有準備,收下禮物後只好撤軍。當作這個義項的時候,「乘」的讀音是「ㄕㄥˋ」。
孟子曾經說過:「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晉國的史書叫《乘》,楚國的史書叫《檮杌》,魯國的史書叫《春秋》。《春秋》容易解釋,記載一年四季的事情。
《檮杌》最難解釋,過去的說法是「檮杌(ㄊㄠˊ ㄨˋ)」是凶獸之名,楚國用它做為史書的書名,是為了懲罰歷史上的惡人;還有學者說,檮杌能夠預知未來,如果有人想要捕捉牠,牠事先就能夠知道,因此用作書名,表示往知來的意思;也有學者說「檮」是木質堅硬的樹,「杌」是砍斷這種樹後剩餘的木樁子,木樁子的橫斷面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輪,因此用來代表歷史,並用作書名。
晉國的史書叫《乘》,宋代學者孫爽解釋道:「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田賦乘馬之事,關乎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大事,故以《乘》為名,後來「史乘」就成為史書的泛稱,即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