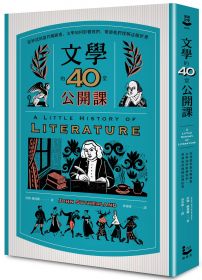1.〈身而為人〉——悲劇
具備完善形式的悲劇,代表著文學長年演化後的新高峰(有人更主張是文學的最高點):內容取材自神話、傳說和史詩,在其上加入「形式」。它們書寫於二千年前,作品語言今天鮮少人能懂,當中的社會和我們根本來自不同世界,那麼我們為何還要閱讀、觀賞這些悲劇呢?答案很簡單。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歐里庇得斯(Euripides) 與其他古希臘劇作家之後,無人的悲劇能出其右。
不過話說回來,「悲劇」究竟是什麼意思?一台大型噴射客機墜機了。雖然不常發生,唉,但天有不測風雲。意外之中好幾百人喪生,國內報紙馬上以頭條報導。《紐約時報》頭版寫著:「天降悲劇:三百八十五人喪生」。《紐約每日新聞》標題更聳動:「三萬九千呎的驚恐事件:上百人遇難!」對於兩報讀者來說,這樣的頭條習以為常。
但我要請大家捫心自問:驚恐的事件和一場悲劇是否能相提並論?
經典悲劇《伊底帕斯王》
約二千五百年前,這個問題在一部戲劇中被鉅細靡遺討論過。它的作者是索福克勒斯,劇作是為雅典觀眾所寫。演出時間是在白天,位於一座戶外的石製圓形劇場,座位成排環繞著舞台。演員們戴著可能有擴音器效果的面具(personae),足蹬高高的長統厚底鞋(buskins),以便後排觀眾也能看清楚他們。演出的舞台音響效果,甚至比紐約百老匯或倫敦西區的劇院更好。如果你去一趟保存最好的埃皮達魯斯古劇場(Epidaurus),導遊會讓你坐在劇場最後一排,然後走到舞台中央劃火柴,而坐在遠處的你仍能清楚聽到劃火柴的聲音。
索福克勒斯的傑作《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故事是以一則古希臘神話為本。發生在過去的事,如今必須「作個了斷」。德爾菲(Delphi)的一名女祭司是著名的預言家,但她的預言也是出了名難以解讀。她預言,底比斯(Thebes)國王萊厄斯和王后約卡絲塔(Laius and Jocasta)會生下一個兒子,而這孩子將來注定弒父娶母,成為天理難容的怪物,底比斯少了他最好—即便這孩子是國王夫婦唯一的孩子,王位繼承在他死後將成為棘手問題。最後,小嬰兒伊底帕斯被帶到山中丟棄等死,但是他沒有死:先是被牧羊人拯救,之後又經歷一連串事件,科林斯(Corinth)的國王和王后收養了身世不明的他。眾神看似特別眷顧他。
伊底帕斯長大成人後,因為傳言他不是父親的親生子,再次請祭司解讀他的命運。祭司警告他,他注定弒父娶母,犯下亂倫之罪。伊底帕斯誤以為祭司指的是養父母,因此逃離科林斯,前往底比斯。在一條岔路上,他遇到另一頭駛來的一輛雙輪戰車。駕車人把伊底帕斯擠到路邊,令他惡言相向,駕車人出手重擊他的頭。就這樣雙方大打出手,伊底帕斯在盛怒下殺死對方,殊不知他正是自己的親生父親萊厄斯。這單純是一場道路糾紛,「一時衝動」而已。
伊底帕斯繼續走上通往底比斯的道路,渾然不知自己的命運。他先遇上人面獅身的斯芬克斯(Sphinx)。牠長年盤踞在山中,威脅著城裡的居民。斯芬克斯會向所有過路人出一道謎題,如果他們答錯便會死。這個謎題是:「什麼動物早晨四隻腳走路,下午兩隻腳走路,晚上三隻腳走路?」伊底帕斯是第一個答對的人。答案是「人類」:嬰兒四肢著地爬行,大人靠雙腿走路,老人則要多拄一根枴杖。斯芬克斯聽他答對便自殺了。底比斯城民對他無比感激,推舉伊底帕斯成為國王。他繼位後為了鞏固王位,娶了守寡的王后約卡絲塔。前任國王萊厄斯為何喪命仍是一場不解之謎,而這兩人便在不知情之下,犯下亂倫之罪。
伊底帕斯和約卡絲塔生下了孩子。他是個好國王、好丈夫、也是個好父親。但幾年之後,底比斯爆發一場神祕的恐怖大瘟疫,好幾千人喪生。非但如此,作物也屢屢欠收,女人無法懷孕。索福克勒斯的戲劇就是從這裡拉開序幕。底比斯城顯然陷入另一場詛咒。但究竟為什麼呢?這時,雙眼全盲的預言家特瑞西亞斯(Tiresias)揭露了背後的可怕真相:眾神懲罰這座城,全是因為伊底帕斯犯下弒親(殺死父親)亂倫(娶了母親)之罪。不論真相有多麼駭人聽聞,終究還是攤在陽光下。最後,王后約卡絲塔上吊自殺,伊底帕斯用妻子的胸針刺瞎自己雙眼,餘生行乞,成為底比斯最低賤的人,女兒安蒂岡妮(Antigone)則不離不棄陪他度過悲慘的餘生。
現在,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伊底帕斯王》為何不只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而是一個悲劇?而且,若要論悲劇,底比斯百姓的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為何比不上一個精神崩潰的盲人乞丐?
亞里斯多德論悲劇
提出這些問題的,是古希臘最偉大的文學評論家:亞里斯多德是。他潛心研究悲劇,尤其是《伊底帕斯王》,並寫下《詩學》(Poetics)一書。雖然《伊底帕斯王》和它的許多譯本都是以韻文寫成,但亞里斯多德將書名取作《詩學》不代表他獨尊詩作,而只是以「詩學」一詞來稱呼文學的技巧,以分析文學的原理。在這本書中,亞里斯多德以《伊底帕斯王》為主要的例子來回答上述問題
他提出一個很有啟發性的矛盾問題當作起手式。比方說,想像你在劇院外遇到一個朋友,她才剛看完莎士比亞的《李爾王》(King Lear)。這齣戲和《伊底帕斯王》極為相似。 「妳喜歡嗎?」你問。「很喜歡。」她說。「這是我這輩子看過最好看的戲。」「妳這冷血的傢伙!」你罵她。「妳居然享受看到一個老人被邪惡的女兒折磨至死,還有另一個老人被弄瞎。妳說妳喜歡?妳下次乾脆去看血淋淋的鬥牛算了。」
當然,這根本是胡說八道。亞里斯多德指出,我們欣賞悲劇之美,觸動我們的不是其中的事件(故事),而是悲劇如何鋪陳(情節)。我們喜歡《李爾王》,不是享受殘酷的事實,而是其中的技法,也就是它的展現/演出(representation)—亞里斯多德稱之為「模仿」(mimesis)。因此,說自己「享受」並無不妥。
接著,亞里斯多德解釋了《伊底帕斯王》為何是悲劇。拿「意外」來說,隨劇情推演,我們漸漸會明白:悲劇中沒有意外。一切都預言過了—所以祭司和預言家才會是悲劇的中心角色。一切自有定數,事情將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結局。我們當下也許茫然不察,但後來就會明白。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當我們看到悲劇慢慢開展時,會感覺所有事件都是「必然且可能成真的」。在悲劇中,發生的事都是無可避免。但是確實明白命定事件背後的所有真相,對血肉之軀的人類來說總是難以承受的。於是,當伊底帕斯終於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同時明白天命難違,他主動實現了預言家的另一項斷言:他是盲目的人。即使那只是個比喻,他還是將自己弄瞎了。人類無法承受沉重的現實。
藉著亞里斯多德的分析,我們像技師拆解汽車引擎一樣,拆解索福克勒斯筆下結構完美的悲劇。他分析,悲劇一定要是關於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上層貴族。皇室人物是最理想的題材(事實上,更古老的時代真的有某位國王叫做伊底帕斯)。亞里斯多德說,以奴隸或女人為悲劇的主角是一件荒謬的事。另外,他堅持悲劇一定要著重「過程」,而且不得失焦。暴力也不能搬上舞台。理想上,就如同《伊底帕斯王》,悲劇必須描述這個悲劇性過程的最後階段。悲劇關心的是棋局中的「殘局」(endgame),也就是結果。
悲劇英雄
現代法國劇作家尚.阿諾伊根據索福克勒斯的另一劇作改編了一部作品,內容關於伊底帕斯的女兒安蒂岡妮。說到他的改編版,他將悲劇情節形容為一具「機械」,每個零件彼此牽動連結,以達到最終的效果,就好比瑞士鐘錶內精密的機械「運作」原理。究竟是什麼機制讓悲劇得以運作呢?亞里斯多德說,每齣悲劇都必須有個觸發點,而悲劇英雄必須自己扣下扳機。他稱之為「悲劇性過失」(hamartia),通常勉強翻譯為「判斷錯誤」。伊底帕斯於盛怒下,在岔路口殺死令人惱火的陌生人,觸發了毀其一生的悲劇。他的脾氣暴躁,父親萊厄斯也是(畢竟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就是伊底帕斯的「過失」或「判斷錯誤」,此舉有如發動汽車的鑰匙,啟動了一連串事件。這台車上路之後,最終將車毀人亡。它之所以令人膽顫心驚,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會犯下這樣的錯誤。
亞里斯多德特別敏銳地指出,觀眾在完整觀賞一齣發揮應有功效的悲劇之後會產生怎樣的回應。他認為悲劇能撼動人心—據他說,曾有懷孕的女人觀賞悲劇而導致早產,悲劇的力量由此可見一斑。他指出,悲劇尤其能讓人感受到「可憐和恐懼」。覺得可憐,是因為同情悲劇英雄的遭遇。感到恐懼,則是因為如果這一切能發生在悲劇英雄身上,那也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包括我們自己。
亞里斯多德的論證裡,最具爭議性的是他所謂的「淨化」(catharsis)理論。這個字無法翻譯,我們通常直接使用亞里斯多德的用語,最好的詮釋是「調和情感」。讓我們回到那位走出戲院的觀眾身上,她剛欣賞完像一齣像《李爾王》或《伊底帕斯王》這樣精采的悲劇。她會感到恍然大悟、思如泉湧。觀賞完舞台上發生的事,觀眾會感到全身筋疲力盡,同時又莫名振奮,好像經歷一場宗教洗禮。
與其將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話奉為圭臬,不如將它視為一套工具。然而,即使相隔了千百年,為何《伊底帕斯王》今天依然能夠打動我們?舉例來說,我們就不苟同亞里斯多德對於奴隸和女人的社會觀;政治上,我們也不認為在國族歷史中,只有國王、王后和貴族值得一提。
有兩個可能的答案。其一是它就如同帕德嫩神廟、泰姬瑪哈陵 或是達文西的畫作,手法精湛,深具美感。其二是即使人類知識大量擴展,生命與人的處境對於思考之人來說仍然充滿神祕。悲劇直接面對這個謎團,檢視人生的大哉問:生命的意義為何?我們何以為人?就目的來說,文學體裁(genre)當中最具野心的便是悲劇。如亞里斯多德所言,悲劇無疑是最「崇高」的文學。
2.〈旅人的荒誕故事〉——笛福、史威夫特和小說的崛起
前一章探索了現代小說的「根」基,現在我們將提到它結成的第一棵熟果。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是《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這本書是眾人公認的英國小說之始。十八世紀上半葉和中葉裡出現多位作家,像是笛福、塞繆爾.理查森、亨利.菲爾丁、強納森.史威夫特、勞倫斯.斯特恩等。在這段期間,我們可以看到現代小說從人類說故事的各種方式中脫穎而出。
我們必須釐清一切從何開始。我們所謂的「小說」(novel,也指「新東西」),為何是此時在倫敦出現?答案是:小說是和資本主義在同一時期、同一地點開始發展,雖然兩者看來相距天差地遠,暗地裡卻息息相關。
「新人類」說故事的方法
不如這麼說吧。魯賓遜.克魯索漂流到島上,設法自給自足,這是新人類創立新經濟系統的過程。經濟學家經常拿他來說明何謂「經濟人」(Homo economicus)。若我們仔細研究笛福的小說,它反映了當時倫敦市的經濟樣貌,包括會計公司、銀行、商店、倉庫、辦公室和泰晤士河的港口。那是個屬於商貿冒險家、資本主義和創業精神的時代。你必須開拓自己的人生,就像白手起家的迪克.威廷頓。你一貧如洗來到城市中,也許能發現這裡遍地是黃金—也或許不行。中世紀的世界裡,農夫不能以成為騎士為志。但是就複雜的人事體系來說,社會階層流動反而是資本主義的主要特色。城市的小書記會希望有朝一日成為產業的領導者,或是像迪克.威廷頓,一躍成為倫敦市長。
就算從未讀過這本書,魯賓遜漂流到荒島上的故事,大概所有人都耳熟能詳。總之,以下是簡單的劇情大綱。一個年輕人和他從商的父親翻臉,身無分文到海上工作。經歷各種冒險之後,他成了貿易商,商品包括奴隸、咖啡和各種值得新、舊世界交易的物品。魯賓遜是「新時代的人」,生逢其時。
在一次出航前往巴西的途中,他的商船遇到暴風雨,所有船員都不幸罹難,他被迫在一座荒島上度過二十八年的歲月。他開拓了那座島嶼。登陸時,他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什麼都沒有,最後離開島嶼時卻坐擁財富。他是怎麼辦到的?靠創業精神。他利用島嶼上的自然資源白手起家。而且,面對各種挑戰時,他從未喪失對神的信心。事實上,他相信這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安排,而祂也贊成魯賓遜在島上的所有作為。這是神的成就,也是他的成就。
書首度在倫敦地區上市時,我們從《魯賓遜.克魯索的奇異冒險和人生》(The Life and strang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封面頁,便能知道小說作為新文學「類型」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一七一九年,第一批讀者看到它時,會先看到「魯賓遜.克魯索」這個名字,再往下讀會看到一行「本人親筆所寫」。笛福的名字並未出現。這本書宣稱魯賓遜的航行和冒險故事都是真實事件。許多第一次閱讀的人自然受到誤導,以為真有人叫魯賓遜.克魯索,而他在南美奧利諾科河(Oronoque River)出口處的一座荒島上獨自存活二十八年,並在那裡致富。
從它面世那一刻起,我們頭一次見識到已臻成熟的敘事傳統:寫實主義。這意味著,書中敘述雖然純屬虛構,但我們若不細究,根本無從分辨。笛福的小說令人混淆,大眾不知道這究竟是真實事件,或只是寫得幾可亂真。其實,這本書問世的四年前,曾有個水手意外漂流到荒島上。他當時的紀錄正如笛福的小說,成了暢銷作品。笛福顯然讀過這份紀錄。不過,那位水手在荒島上並未致富,甚至日子過得很難熬。那畢竟是人生,不是虛構故事。一七一九年,天真的讀者乍看封面頁,絕對想不到《魯賓遜漂流記》不是另一個「真實的」冒險家故事。
不知情的讀者看到《魯賓遜漂流記》的開頭段落,會以為這是一本真實的自傳。試讀以下段落,看你能否發覺它純屬虛構:
「我在一六三二年出生於約克市,家世算好,但我們家其實不是本地人,我父親的故鄉在德國不來梅,剛到英國時是在赫爾落腳。他靠經商買了塊地,後來離開那一行,定居約克市,並娶了我母親為妻。我母親娘家姓魯賓遜,是當地的名門望族,父母因此將我取名為魯賓遜.古魯茨涅爾。但英國人都亂唸我們家的姓,後來我們家族便被稱為……不,後來我們乾脆自稱「克魯索」家族,簽名也索性改了。於是,朋友也就這麼稱呼我了。」
這讀起來像是「真人真事」,主角是一個本來姓古魯茨涅爾、現在姓克魯索的人。隨故事推演,克魯索經歷了一連串刺激的冒險。這也是年輕讀者熱愛這本小說的原因。他差點淹死、被海盜抓住,還成了阿拉伯人的奴隸。他歷經千辛萬苦,最終成為南美的有錢人,擁有農莊(和奴隸)。但後來他為了賺更多錢而再次出航,卻失去了一切,獨自流落荒島。就最單純的敘述層次來說,這故事確實令人難以釋卷。在沒有補給,沒有其他人幫忙之下,我們的主角要如何克服萬難、對抗野生動物和食人族?但我們心底會暗自期待他成功。更深一層來說,克魯索便是如假包換的經濟人。他的故事就是關於財富和創造財富。如同精采情節和冒險故事,這主題同樣扣人心弦。
船難之後,克魯索趁著船還沒全毀、東西尚未沉入海裡之前,數次冒險回到船上。他乘著臨時打造的木筏,拿回了所有他希望未來能派上用場的物品。他鉅細靡遺地告訴我們他搶救了哪些東西,包括他在船長保險箱找到的三十六英鎊。雖然他知道在荒島上錢一無是處,也知道此舉形同偷竊,他仍把錢帶走了。這件事別具意義。什麼最重要?錢。這個事件再次提醒我們這件事。
接下來的二十八年,克魯索用他帶上岸的東西過活,並慢慢開墾島嶼。島上一切都是他的財產。他自立為島嶼之「王」。從這角度來看,我們可說《魯賓遜漂流記》是帝國的縮影,也象徵英國。該時期,英國正在全球不斷擴張帝國版圖。
許多年後,克魯索多了個夥伴,一個從附近島嶼食人族手中逃脫的當地人。克魯索因為是在星期五找到他,便將他命名為「星期五」,並讓他成為自己的僕人。這段情節的重點是,星期五是他的資產,更直白來說,他是奴隸。帝國永遠需要奴隸。
丹尼爾.笛福是英國文學中最令人關注、多才多藝的作家之一。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以當時標準而言),不但寫過評論時事的小冊子,更曾經從商、投資當時還是新發明的股票。他也是政府間諜,還獲公認為「英國新聞業之父」,生前寫過幾百本書、小冊子和報刊。他的生活不曾富裕,偶爾觸犯法律,晚年生活幾乎窮途潦倒—但也是在這時期開創了我們現在所知的英文小說。維吉尼亞.吳爾芙要女人在艾芙拉.班恩墳上獻花,那麼我們便該在丹尼爾.笛福墳前獻上英鎊和紙鈔,因為他記錄了一個經濟人的故事
融合真實與幻想
小說是自由的,不必然侷限於笛福嚴格的寫實主義。小說也可以充滿「奇幻想像」,一方面維持寫實的外部結構,一方面又能像童話一般富有想像力。所謂「奇幻小說」的偉大開拓者,是強納森.史威夫特(Johnathan Swift, 1667-1745)。
史威夫特是愛爾蘭人,出身「新教優越階級」(the Ascendancy)。這是當時受英國人支持的愛爾蘭上層階級,因此得以在社會上享有大半愛爾蘭人口所沒有的特權。他一生多半待在祖國,被視為第一位偉大的愛爾蘭作家。他在都柏林三一學院受高等教育,後來成為學者。他頗具野心,遠赴英國擔任貴族的秘書,期待生涯能有進一步發展。這個時代,想進一步發展就需要有人資助。在那個世界,人還無法單打獨鬥。
史威夫特的資助者將他介紹給王室,灌輸他托利黨(Tory,後來的保守黨)思想,他也終生抱持此一立場。他最後取得了神學博士學位—因此大家通常稱呼他「史威夫特博士」—並受命為愛爾蘭新教教堂牧師。史威夫特博士講道多年,最後當上都柏林聖派翠克大教堂座堂主任牧師,但從未如願得到英國王室和政府重用。他為此憤恨不平,甚至口出惡言。他說他感覺自己「像洞裡的老鼠」。
一七二○年代,《魯賓遜漂流記》成為暢銷書時,史威夫特開始著手撰寫他的代表作《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和《魯賓遜漂流記》一樣,這本書在一七二六年出版時也佯裝成真實的「旅人故事」。當時不少人都上了當。書裡描寫了四段旅程。主人翁抵達的第一個地方是小人國「厘厘普」(Lilliput),當地的人體型嬌小,卻認為自己至關重要。史威夫特以此嘲諷安妮女王周遭的朝臣和佞臣。第二趟旅程,格列佛來到大人國「布羅丁那格」(Brobdingnag),居民是住在鄉村的巨人。這一回,換成主人翁在相較之下有如小人偶。史威夫特創造的四個國家中,布羅丁那格是最舒適的一個國家,一切都很老派和傳統,各方面都「不現代」。史威夫特痛恨進步。
這份厭惡在第三趟旅程中清楚可見。格列佛到了「拉普塔」(Laputa);西班牙文中,這個字代表妓女。那是一座科學化的理想國度,而史威夫特厭惡科學,覺得它毫無必要性,而且違背信仰。他在書中將當時的資深科學家刻畫成書呆子,還自找麻煩,試圖萃取小黃瓜中的陽光。這趟旅程中也寫到了「斯卓布拉格人」(Struldbrug),這群人永遠不會死,但也永遠在凋零,無止境地承受折磨和痛苦,心靈也衰弱不堪。他們身心靈盡皆崩潰,卻怎麼也死不了。一次次的旅程變得愈來愈可怕。
第四趟旅程最令人摸不著腦袋。格列佛來到了慧駰國(Houyhnhnm Land)。「慧駰」的發音代表馬嘶聲。這裡是由馬當家作主,人類被刻畫為隨地便溺、愚蠢骯髒的猿猴「犽猢」(Yahoo)。由於馬匹只吃穀粒和草,因此排洩物氣味較不刺鼻。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認為,這裡或許可以一窺史威夫特對於生命中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奇特見解。當然,馬匹沒有科技、機構、「文化」和文學,所以在慧駰國也沒有這些東西。然而,這裡很顯然是史威夫特所刻畫最接近「烏托邦」的地方。他對人類未來不抱太大的希望。
和魯賓遜的冒險一樣,《格列佛遊記》以創新的方式將真實和幻想融合,為後續幾世紀的無數小說開拓了一條康莊大道。對所有人來說,想在美好的虛構故事世界裡展開一段冒險旅程,這兩本書是最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