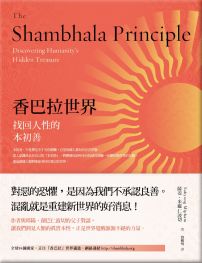■「蕯姜」喚醒人們覺察自己的「本初善」
從早年開始,我內心深處雖然知道「薩姜」將是我在此生扮演的角色,但在父親正式為我授權登位後,我才意識到自己並不真的明白「成為一位薩姜」是什麼意思。當我問父親「薩姜」要做些什麼事時,他回答說:「薩姜喚醒人們覺察自己的本初善。」
就這樣嗎?我想,做為一個「薩姜」絕不可能是那麼簡單的,可能就這樣嗎?他說的「人類基本是善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如果這是真的,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苦難?這就像是一個禪宗公案或冥思的課題。我沒想到的是,在接下來的三十五年間,我都在試著搜尋、了解,並經驗父親所教給我這件事的單純性與複雜性。
父親希望我的研習要對應於他自己後半生的教育,反映出東方與西方間的一種平衡。我承繼了自己的靈修傳統,以其深奧的智慧來學習佛教哲學與金剛乘密法的教義。多年來,我也學習了西方的思想、哲學、政治、經濟學、詩歌與文學。在體能上,我受過射箭、馬術、武術等訓練,因此我的養成教育是既古典又現代的。此外,我還在亞洲與西方世界修習禪修和思惟修的方法。我的訓練和修行告訴我,學習本身並不會導致智慧,而是通過自我反思,去內化我所學到的一切,並在日常生活中嘗試應用它們,然後反省其效果,這才是臻至智慧的過程。
當父親在一九八七年圓寂時,我被拱入一個更深層次的內化過程。我當時只有二十四歲,失去了他,不論對我個人或「香巴拉社群」(Shambhala community)與整個世界而言,都是一巨大痛苦與混亂的時期。由於身為他的法嗣,我必須接替他的志業,然而,我覺得自己既未準備好,也無能跟隨他的腳步。那時我尚年輕,需要鍛鍊一己的靈修道徑,眼前的那條路似乎是前途未卜。儘管如此,從一種責任感和對父親的摯愛中,我繼續研習、修行佛教,試著走在香巴拉的勇士之道上。
這一段時期中,時或充滿困難和挑戰。我不僅正在深化靈修上的體悟,在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中,我還被要求去領導一個龐大而多元的「香巴拉社群」。同時,我更面對著信徒的失落、不安全感、憤怒與惶惑。除此之外,我更感受到雙肩擔負著持續那具有數千年歷史傳承的巨大責任─它現在由我來取決應該如何向前邁進。我不僅要了解自己傳統的精髓,而且必須決定如何在現代文化的背景之下延續它。我不斷地受到「香巴拉社群」與世界的全面試煉,有時,人們或鼓勵我不要去關注世界的一般困境,而應該把焦點放在自己的傳統之上。然而,當我繼續扮演一位領導者的角色時,我開始認識到,在靈性與世俗的種種努力中,「人性」的觀點不斷生起,而我每天都受到思惟「什麼是本初善」的挑戰。
在這段期間裡,我經常思索父親想要超越他靈修界限的藩籬,而進入這充滿全球性經濟、政治與環境問題之世界的願望。只是做為一名西藏喇嘛與上師可能較為安全、簡單得多,然而,那就不是我父親了,更重要的是,那不是他覺得的自己。
他的上師曾告訴他,他們所熟悉、摯愛的世界已經結束了,現在將由他來傳遞西藏智慧的本質─人與社會是良善美好的,這超越佛教或任何宗教的參考依據。他看到了為能達此目的,最好的方法是承擔起一位「大地護佑者」之責,使眾生於其良善中覺醒,以期保護此良善。
■「香巴拉」即勇氣與良善的原則
我問自己,為什麼如此卓絕明智之人,會去強調「本初善」如此一個簡單的訊息?我父親是一個極度信任人類本性的人。不論在東方或西方,他總是在綜合自己所獲得的知識,不僅是去理解和比較佛陀所教,也去評比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耶穌、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的教義,以及中國崇高的思想家如老子與孔子之教。他還特別尊重印度偉大的統治者阿育王(King Ashoka)、日本的聖德太子和禪宗傳統的道元禪師。雖然這些傳統各不相同,但皆可濃縮集中為兩個簡單的觀點─人類是良善的,而良善是社會的本性。
透過研究和思考,我開始感覺到自己內在對「香巴拉原則」之理解的轉變,我理解到它是一種潛在的普遍主題,存在於整個人類思想明顯的與晦澀的理路中。這種普遍性並非任何傳統的「稀釋」,它是所有傳統的核心。它不是我們創造出來的事物,而是我們能發現到的事物。
「香巴拉」(Shambhala)一詞意指「幸福的源泉」(source of happiness),正如我先前所述,它本是一個中亞古王國的名字,也被稱為「香格里拉」(Shangri- La)。據古代佛教典籍所述,它曾存在於西元前五世紀,通常稱其為「北方的香巴拉」(Shambhala of North)。對於我父親而言,「香巴拉」則是勇氣與良善之原則的同義詞。
傳說中的香巴拉曾是一個具體存在於地球上的國家,其子民對「本初善」已達到甚深的了悟,而皆一同證道。依據傳說,在那一刻,整個王國超越了與形體有關的物質世界。也有人說香巴拉依然存在,它體現在略微超出我們概念心能掌握的一種境界。
根據傳說,香巴拉坐落於東方的西部和西方的東部,即亞洲、歐洲與阿拉伯世界的匯合處。因此,即使在地理上,香巴拉也處於一種全然普遍性的位置。香巴拉的子民據說具有先進的科技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智能。為了建立覺悟的社會,他們激發起一己的良善,將之應用於日常生活中,這又成為對此覺悟的恆常支持。他們灌注了仁慈、悲憫於人際關係中,也用它們來發展此類素質,這一切都源於對人類本具智慧的一種共同信念,而此一傳說正是我父親靈感的來源:在這些偉大文化的交匯處,良善的精神受到讚美和慶祝,它即是人性實踐與文化成就的典型。
香巴拉不僅是一個處所,它更是一條靈修的道徑,有時也被稱為「屬世之道」(a worldly path),因為對「本初善」的信心讓我們放鬆於自己的世界,而能看到它的神聖品質。即使在一般的意義上,當我們能欣賞某事物時,這就意味著我們已經能夠讓自己放鬆並接受它。當我父親親睹香巴拉之時,他是在展示一種禪修冥想的能力;以此等純粹的感知,他可以看到個人和社會當下便是覺悟的。若光是閱讀每天頭條新聞的報導,我們也許無法想像那種覺悟的情境,但視「社會是覺悟的」其實是一個現實可行的方法,因為除此世界之外,並無有其他的世界可以逃躲。
與此同時,覺悟的社會並不是一個烏托邦,而是一種處所,在那裡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去看,並且去存在—只是做自己,放棄奢望其他更美好之事物的幻想。當我們這麼做時,在此星球上發現一己的良善,就變成了一種欣賞與讚嘆的修習。
放慢腳步、自我省察並感受到自己的價值,而且對此充滿信心,便可以產生空間感,然後我們會擁有真實的智慧,知道該走往哪個方向。然而,我們被膚淺的樂趣和恐懼所哄騙而昏沉麻痹,絕大多數人缺乏對「本初善」
的信心,因為每天的生活都是挑戰,而且還有甚多的機會讓我們認為人性是低劣的。在自我反省之後,我們會問:我們「感覺」如何呢?當我們與自己的心相連結時,會發現什麼呢?無論生活是何等地艱辛,「本初善」不會因情境而受到稀釋,因為它是不會改變的。障礙和挑戰或會時時出現,但它們並不會減少我們可掌握、運用的覺悟品質。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人可以感受到一己的善良,那麼,在一段艱苦困難的時期中,社會將不致破敗,實際上會變得更加強大。……………
【精髓指導】(摘錄)
■父親的彈指與微笑
向父親詢問什麼是「本初善」時,其結果往往會是詩歌的呈現。他會寫一首詩,或要我來寫一首。有時,他會彈指或微笑,或以其他一些手印去碰觸我的心,或只是凝視著我。在最高層次的佛法裡,這些被稱為「精髓指導」(essential instructions)。於此類的傳法中,學人被引入深刻的主題,例如愛、空性、明性與慈悲等,這些都難以用言語文字來形容。運用詩歌、藝術或手印的形式,是因為在知性的理解之外,詩歌、藝術或手印皆能讓感覺生起。
在接受這樣的傳法之前,我的研修前行是必須努力去記誦或分析古籍裡關於空性、大樂(bliss)與其他深奧的主題,使我可以熟悉於那些大成就者是如何去理解人性的。研習課程也包含討論與辯論,這些練習的關鍵是要熟悉人性的層面,讓我能夠內化它們,並明確表達我的理解。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曾指出讓學生作研習與訓練的必要,以使他們具體展現真理。正如西藏體系,古希臘人也利用研究與對話來幫助學生將概念轉化成體驗。
一開始時,因為我們的心總執迷於事物的表象,要體驗事物的本性是頗具挑戰性的;我們無法想像事物的本性,也不能感知它。香巴拉的傳統採用了「鏡子」的意象來表徵「本初善」容納全體的特質。此鏡被稱為「宇宙(之鏡)」,因為它映照一切;它是「宇宙性的」(cosmic),因其超越了傳統常規上的概念,包括空間與時間。因此,事物的本性被認為是本初的,而且是超越時間的。鏡子裡的影像與鏡子本身並不能分開,就如同清晨的天空融入一片湖面之中。因此,宇宙之鏡反映了世界根本的智慧─它含括一切,恆常在無限的開放性中源源不斷生起。
父親告訴我,「本初善」不單是一種人類的現象,或只有在禪定中才能經驗的事物;相反地,它是鮮活的,以作為貫通宇宙的一種基本能量在嗡嗡低鳴著,極為平常無奇。他經常利用野外來向我介紹事物的本性,我們或會坐在大地上,可以聞到草香,感受那輕風拂面、陽光的溫暖,並看著雲朵飄過眼前。有時,我們還會在花園裡工作─挖土、澆水,並觸摸土壤和植物。花園可以讓我們與季節連接起來;由於植物總是對天氣與季節的變化作反應,因此這是對「當下此刻」(nowness)一種不斷的提醒。
■一切皆全善,無一物不善
當隨學父親的教導所得的體驗日漸增長時,我對「本初善」的理解變得較少概念性,而更具經驗性。我開始看到,雖然地、水、火、風各有不同的特質,雖然它們的展現總在不斷變化,但其本質是相同的,如同陽光映照在鑽石上閃閃發光。
在這些元素中有一種範圍極廣的溝通力量,「溝通」是一條以和諧來運作的雙行道。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臉龐與身形,但不知何故,我們的心卻是十分類似的。從心來表達,同時也了解到我們都擁有相同的心,可產生那幫助人們實現其智慧與慈悲的和諧感,而最終的結果將是解脫。
許多種語言和文化都談到這一鮮活的感覺,以及當我們確信它時所產生的信心。偉大的中國先哲孟子提到,人性的本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仁慈,這是完備富足的人心洋溢著愛與利他主義。在《尼各馬科倫理學》(Nichomachean Ethics)的開篇行首,亞里士多德寫道:「所有事物皆理所當然地明宣歸於『善』。」十四世紀西藏最卓越傑出的聖哲之一龍欽巴(Longchenpa)尊者則說:「因一切皆全善,無一物不善,萬物皆等同於完全善好的狀態,其中既非好亦非壞。」
當我剛剛認識「本初善」時,我得記住它的特質─它是不變的、無始無終的,且能涵納一切;在每個定義下,更有其子類別。我們的真實本性以智力、純淨的能量、正念、存在與直覺來表達自己;它也含有「知識」這一元素。同樣地,所有外在的知識都在讓我們內在的「本初善」覺醒,因為人類本質上是「能認知的」生物。「本初善」不同於「資訊」,它不能被傳輸,而只能被指點出來,此心必須於那原本已然存在的事物中覺醒。當我們認識到並信任一己的原始本性,我們對其具有信心時,便是那勇於保持開放的心靈與心智,並將它們提供給世界的勇士;但當我們懷疑自己的本性時,我們就是躲避世界的懦夫,害怕承認自己存在之根源的開放性。這是我們所必須面臨的抉擇。
人類透過好奇、愛、理解,甚至是悲傷或痛苦的心念,不斷地經驗著自己內心的開放性。因為我們活著,這些深層的感覺總在湧現,以感官來和世界連結。藉由專注心念並感覺此心,我們便增加了自己與良善連結的能力。所以,我們要花一點時間來聚集感官,將之收攝入心,去感覺「有價值」所意味的是什麼。這能點燃信心──那可以喚醒能量的火花,我們的生命於是被此健全之光所照亮。
當我們接觸到自己的能量,就能體驗環境的能量。我們看到世界是鮮活的,具有其有形可觸的、基本的「風馬」(windhorse)能量─那未造作的生命精神。一旦意識到這種穩定的覺醒力量,我們便可以一直連接上它。我們與環境相互依存的關係也是覺悟社會的一種表現,通過調和自己的感知,每一刻都呈現給我們讓生命覺醒的機會,例如,真正地品嚐到所吃的食物,或聽到雷鳴。
當我父親移居到西方世界, 他注意到, 有時我們認為為了成為「 靈性的」(spiritual),就需要關閉自己感官的知覺。他說:「我們覺得必須將它們轉換成某種虛構的、事物應該像什麼的概念。」但當我們閉鎖自己的感知,就會使自己的自然能量日漸麻痹,因而脫離了自己的生命。我們變得以思辨為主,在智性上與情感上皆與環境隔離,並失去感覺的能力。缺乏感覺,我們就不再全然地存在於這個星球上了,因為我們已經失去關懷的能力。這便是仁慈與悲憫開始減弱的原因。如果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這將是一種無可衡量的巨大悲劇。
我父親說過:「任何的感知,都可以使我們與現實全然而充分地連接起來。」「當下」(Now)通過我們的觸覺、味覺、視覺、聽覺和嗅覺來宣告自身。你現在聞到什麼呢?當我們完全欣賞自己的感知,即是良善被表達出來的時刻。每一刻都覺得鮮活,我們與事物之本然面貌相連結─紅色是紅的;一匹賽馬正是一匹賽馬。我們已經聽聞到「本初善」,但只有在真心與之遭遇後,我們方覺得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