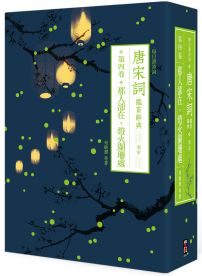〈青玉案〉 辛棄疾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寫上元燈節的詞,不計其數,稼軒的這一首,卻誰也不能視為可有可無,即此亦可謂豪傑了。然究其實際,上片也不過渲染那一片熱鬧景況,並無特異獨出之處。看他寫火樹,固定的燈彩也。寫「星雨」,流動的煙火也。若說好,就好在想像:是東風還未催開百花,卻先吹放了元宵的火樹銀花。它不但吹開地上的燈花,而且還又從天上吹落了如雨的彩星──燃放煙火,先衝上雲霄,復自空而落,真似隕星雨。然後寫車馬,寫鼓樂,寫燈月交輝的人間仙境──「玉壺」,寫那民間藝人們的載歌載舞、魚龍曼衍的「社火」百戲,好不繁華熱鬧,令人目不暇接。其間「寶」也,「雕」也,「鳳」也,「玉」也,種種麗字,總是為了給那燈宵的氣氛來傳神來寫境,蓋那境界本非筆墨所能傳寫,幸虧還有這些美好的字眼,聊為助意而已。總之,我說稼軒此詞,前半實無獨到之勝可以大書特書。其精彩之筆,全在後半始見。
後片之筆,置景於後,不復贅述了,專門寫人。看他先從頭上寫起:這些遊女們,一個個霧鬢雲鬟,戴滿了元宵特有的鬧蛾兒、雪柳,這些盛妝的遊女們,行走之間說笑個不停,紛紛走過去了,只有衣香猶在暗中飄散。這麼些麗者,都非我意中關切之人,在百千群中只尋找一個──卻總是蹤影皆無。已經是沒有什麼希望了……忽然,眼光一亮,在那一角殘燈旁側,分明看見了,是她!是她!沒有錯,她原來在這冷落的地方,還未歸去,似有所待!
這發現那人的一瞬間,是人生的精神的凝結和昇華,是悲喜莫名的感激銘篆,詞人都如此本領,竟把它變成了筆痕墨影,永誌弗滅!讀到末幅煞拍,才恍然徹悟:那上片的燈、月、煙火、笙笛、社舞交織成的元夕歡騰,那下片的惹人眼花繚亂的一隊隊的麗人群女,原來都只是為了那一個意中之人而設,而寫,倘無此人在,那一切又有何意義與趣味呢!多情的讀者,至此不禁涔涔淚落。
此詞原不可講,一講便成畫蛇,破壞了那萬金無價的人生幸福而又辛酸的一瞬的美好境界。然而畫蛇既成,還思添足:學文者莫忘留意,上片臨末,已出「一夜」二字,這是何故?蓋早已為尋他千百度說明了多少時光的苦心痴意,所以到得下片而出「燈火闌珊」,方才前早呼而後遙應,筆墨之細,文心之苦,至矣盡矣。可嘆世之評者動輒謂稼軒「豪放」,「豪放」,好像將他看作一個粗人壯士之流,豈不是貽誤學人乎?
王靜安《人間詞話》曾舉此詞,以為人之成大事業者,必皆經歷三個境界,而稼軒此詞之境界為第三即最終最高境。此特藉詞喻事,與文學賞析已無交涉,王先生早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無勞糾葛。
從詞調來講,〈青玉案〉十分別致,它原是雙調,上下片相同,只上片第二句變成三字一斷的疊句,跌宕生姿。下片則無此斷疊,一連三個七字排句,可排比,可變幻,總隨詞人之意,但排句之勢是一氣呵成的,單單等到排比完了,才逼出煞拍的警策句。北宋另有賀鑄一首,此義正可參看。(周汝昌)
〈揚州慢〉 姜夔
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①,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荳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②,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註〕① 杜牧〈贈別二首〉其一:「娉娉褭褭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② 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這首詞寫於宋孝宗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冬至日,詞前的小序對寫作時間、地點及寫作動因均作了交代。姜夔因路過揚州,目睹了戰爭洗劫後揚州的蕭條景象,撫今追昔,悲嘆今日的荒涼,追憶昔日的繁華,發為吟詠,以寄託對揚州昔日繁華的懷念和對今日山河殘破的哀思。
這首詞在藝術表現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寫景物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景中含情,化景物為情思。它的寫景,不俗不濫,緊緊圍繞著一個統一的主題,即為抒發「黍離之悲」服務。詞人到達揚州之時,是在金主完顏亮南犯後的十五年。他「解鞍少駐」的揚州,位於淮水之南,是歷史上令人神往的「名都」,「竹西佳處」是從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化出。竹西,亭名,在揚州東蜀崗上禪智寺前,風光優美。但經過金兵鐵蹄蹂躪之後,如今是滿目瘡痍了。戰爭的殘痕,到處可見,詞人用「以少總多」的手法,只攝取了兩個鏡頭:「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和滿城的「廢池喬木」。這種景物所引起的意緒,就是「猶厭言兵」。清人陳廷焯特別欣賞這段描寫,他說:「寫兵燹後情景逼真。『猶厭言兵』四字,包括無限傷亂語,他人累千百言,亦無此韻味。」(《白雨齋詞話》卷二)這裡,作者使用了擬人化的手法,連「廢池喬木」都痛恨金人發動的戰爭,物猶如此,何況於人!
上片的結尾三句「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卻又轉換了一個畫面,由所見轉寫所聞,氣氛的渲染也更加濃烈。當日落黃昏之時,悠然而起的清角之聲,打破了黃昏的沉寂,這是用音響來襯托寂靜。「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來是天氣給人的觸覺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說「吹寒」,把角聲的淒清與天氣聯繫在一起,把產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凸出人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角聲把寒意散布在這座空城裡。聽覺所聞是清角悲吟,觸覺所感是寒氣逼人,再聯繫視覺所見的「薺麥青青」與「廢池喬木」這一切交織在一起,一切景物在空間上來說都統一在這座「空城」裡,「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聯繫在一起,同時化景物為情思,將景中情與情中景融為一體,來凸出「黍離之悲」。
用今昔對比的反襯手法來寫景抒情,在這闋詞中是比較凸出的。上片用昔日的「名都」來反襯今日的「空城」;以昔日的「春風十里揚州路」來反襯今日的一片荒蕪景象──「盡薺麥青青」。下片以昔日的「杜郎俊賞」、「荳蔻詞工」、「青樓夢好」等風月繁華,來反襯今日的風流雲散、對景難排和深情難賦。以昔時「二十四橋明月夜」的樂景,反襯今日「波心蕩、冷月無聲」的哀景。「波心蕩、冷月無聲」,是非常精細的特寫鏡頭。「二十四橋仍在」,明月夜也仍有,但「玉人吹簫」的風月繁華已蕩然無存了。詞人用橋下「波心蕩」的動,來映襯「冷月無聲」的靜。「波心蕩」是俯視之景,「冷月無聲」本來是仰觀之景,但映入水中,又成為俯視之景,與橋下蕩漾的水波合成一個畫面,從這個畫境中,似乎可以看到詞人低首沉吟的形象。總之,寫昔日的繁華,正是為了表現今日之蕭條。
善於化用前人的詩境入詞,用虛擬的手法,使其波瀾起伏,餘味不盡,也是這首詞的特色之一。〈揚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詩句與詩境(有四處之多),又點出杜郎的風流俊賞,把杜牧的詩境,融入自己的詞境;但他的追昔,主要懷念的是揚州的風月繁華與風流俊賞,這多少削弱了嚴肅的愛國主義的主題。
詞的下片,較多地使用了虛擬的手法。詞人設想:杜牧如果重遊揚州,面對今日的蕭條,也會感到驚心,即使像杜牧那樣才華橫溢的詩人,怕也「難賦深情」了。「算而今、重到須驚」的「算」字,「縱荳蔻詞工」的「縱」字,「念橋邊紅藥」的「念」字,都是虛擬和加強語氣的字眼。特別是結束處的虛擬,更耐人尋味。冬至之日,本來不是紅芍藥花開的季節,但縱使冬去春回,來日紅藥花開,又有誰來欣賞它呢?花開依舊,人事已非,花開也不過徒增空城的感傷而已。詞情跌宕濃烈,增強了藝術感染力。(劉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