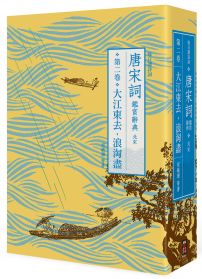〈玉樓春〉歐陽脩
尊前擬把歸期說,欲語春容先慘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
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北宋初年的一些名臣,如范仲淹及晏殊、歐陽脩等人,除德業文章以外,他們也都喜歡填寫一些溫柔旖旎的小詞,而且在小詞的銳感深情之中,更往往可以見到他們的某些心性品格甚至學養襟抱的流露。就歐陽脩而言,則他在小詞中所經常表現出來的意境,可以說乃是一方面既對人世間美好的事物常有著賞愛的深情,而另一方面則對人世間之苦難無常也常有著沉痛的悲慨。這一首〈玉樓春〉詞,可以說就正是表現了其詞中此種意境的一首代表作。
這首詞開端的「尊前擬把歸期說,欲語春容先慘咽」兩句,表面看來固僅是對眼前情事的直接敘寫,但在其遣辭造句的選擇與結構之間,歐陽脩卻已於無意間顯示出了他自己的一種獨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語彚而言,第一句的「尊前」,原該是何等歡樂的場合,第二句的「春容」又該是何等美麗的人物,而在「尊前」所要述說的卻是指向離別的「歸期」,於是「尊前」的歡樂與「春容」的美麗,乃一變而為傷心的「慘咽」了。在這種轉變與對比之中,雖然僅只兩句,我們卻隱然已經能夠體會出歐陽脩詞中所表現的對美好事物之愛賞與對人世無常之悲慨二種情緒相對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種張力了。
其次再就此二句敘寫之口吻而言,歐陽脩在「歸期說」之前,所用的乃是「擬把」兩個字;而在「春容」、「慘咽」之前,所用的則是「欲語」兩個字。曰「擬」、曰「欲」,本來都是將然未然之辭;曰「說」、曰「語」,本來都是言語敘說之意。表面雖似乎是重複,然而其間卻實在含有兩個不同的層次,「擬把」仍只是心中之想,而「欲語」則已是張口欲言之際。二句連言,不僅不是重複,反而更可見出對於指向離別的「歸期」,有多少不忍念及和不忍道出的宛轉的深情。其間固有無窮曲折吞吐的姿態和層次,而歐陽脩筆下寫來,卻又表現得如此真摯,如此自然,如此富於直接感發之力,所以即此二句,實在便已表現了歐詞的一種特美。
至於下面二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則似乎是由前二句所寫的眼前的情事,轉入了一種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對於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廣到了對於整個人世的認知。所謂「人生自是有情痴」者,《世說新語.傷逝》有云:「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所以清況周頤在其《蕙風詞話》中就曾說過:「吾聽風雨,吾覽江山,常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在。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這正是人生之自有情痴,原不關於風月。李後主之〈虞美人〉詞曾有「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句,夫彼天邊之明月與樓外之東風,固原屬無情,何干人事?只不過就有情之人觀之,則明月東風遂皆成為引人傷心斷腸之媒介了。所以說「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此二句雖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實上卻是透過了理念才更見出深情之難解。而此種情痴則又正與首二句所寫的「尊前」、「欲語」的使人悲慘嗚咽之離情暗相呼應。所以下半闋開端乃曰「離歌且莫翻新闋,一曲能教腸寸結」,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闋的尊前話別的情事。「離歌」自當指尊前所演唱的離別的歌曲,所謂「翻新闋」者,殆如白居易〈楊柳枝〉所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與劉禹錫同題和白氏詩所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歐陽脩〈采桑子〉組詞前之〈西湖念語〉,亦云「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蓋如〈陽關〉舊曲,已不堪聽,離歌新闋,亦「一曲能教腸寸結」也。前句「且莫」二字的勸阻之辭寫得如此叮嚀懇切,正以反襯後句「腸寸結」的哀痛傷心。
寫情至此,本已對離別無常之悲慨陷入極深,而歐陽脩卻於末二句突然揚起,寫出了「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的遣玩的豪興,這正是歐陽脩詞風格中的一個最大的特色,也是歐陽脩性格中的一個最大的特色。我以前在《靈谿詞說》中論述馮延巳與晏殊及歐陽脩三家詞風之異同時,就曾指出過他們三家詞雖有繼承影響之關係,然而其詞風則又在相似之中各有不同之特色,而形成其不同之風格特色的緣故,則主要在於三人性格方面的差異。馮詞有熱情的執著,晏詞有明澈的觀照,而歐詞則表現為一種豪宕的意興。歐陽脩這一首〈玉樓春〉詞,明明蘊含有很深重的離別的哀傷與春歸的惆悵,然而他卻偏偏在結尾寫出了「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的豪宕的句子。在這二句中,不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盡」,表現了一種遣玩的意興,而且他所用的「直須」和「始共」等口吻也極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卻畢竟有「盡」,「春風」也畢竟要「別」,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實在隱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論及歐詞此數句時,乃謂其「於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其實「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不僅道中了〈玉樓春〉這一首詞這幾句的好處,而且也恰好說明了歐詞風格中的一點主要的特色,那就是歐陽脩在其賞愛之深情與沉重之悲慨兩種情緒相摩蕩之中,所產生出來的要想以遣玩之意興掙脫沉痛之悲慨的一種既豪宕又沉著的力量。在他的幾首〈采桑子〉小詞,都體現出此一特色。不過比較而言,則這一首〈玉樓春〉詞,可以說是對此一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葉嘉瑩)
〈念奴嬌〉 蘇軾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清代詞論家徐釚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概,固是英雄本色」(《詞苑叢談》卷三)。在《東坡樂府》中,最具有這種英雄氣格的代表作,恐怕要首推這篇被譽為「古今絕唱」(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的〈赤壁懷古〉了。這篇詞是北宋詞壇上最為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它寫於宋神宗元豐五年(一○八二)七月。當時,由於蘇軾詩文諷喻新法,為新派官僚羅織論罪貶謫到黃州,這首詞是他遊賞黃岡城外的赤壁磯時寫下的。
此詞上闋,先即地寫景,為英雄人物出場鋪墊。開篇從滾滾東流的長江著筆,隨即用「浪淘盡」,把傾注不盡的大江與名高累世的歷史人物聯繫起來,布置了一個極為廣闊而悠久的空間時間背景。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洶湧奔騰,又使人想見風流人物的卓犖氣概,更可體味到作者兀立江岸憑弔勝地雄傑所誘發的起伏激盪的心潮,氣魄極大,筆力非凡。接著「故壘」兩句,點出這裡是傳說中的古代赤壁戰場。在蘇軾寫此詞的八百七十多年前,即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二○八),東吳名將周瑜曾在長江南岸,指揮了以弱勝強的赤壁之戰。當年的戰場究竟在哪兒?向來眾說紛紜,東坡在此不過是聊借懷古以抒感,讀者不必刻舟求劍。「人道是」,下字極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詞題,又是為下闋緬懷公瑾預伏一筆。以下「亂石」三句,集中描寫赤壁雄奇壯闊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亂地高插雲霄,洶湧的駭浪猛烈地搏擊著江岸,滔滔的江流捲起千萬堆澎湃的雪浪。這種從不同角度而又訴諸於不同感覺的濃墨健筆的生動描寫,一掃平庸萎靡的氣氛,把讀者頓時帶進一個奔馬轟雷、驚心動魄的奇險境界,使人心胸為之開闊,精神為之振奮!煞拍二句,總束上文,帶起下片。「江山如畫」,這明白精切、脫口而出的讚美,應是作者和讀者從以上大自然的雄偉畫卷中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結論。「地靈人傑」,錦繡山河,必然產生、哺育和吸引無數出色的英雄,三國正是人才輩出的時代:橫槊賦詩的曹操,馳馬射虎的孫權,隆中定策的諸葛亮,赤壁破敵的周公瑾……真可說是「一時多少豪傑」!
上片重在寫景,將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緊縮集中到三國時代的風雲人物身上。但蘇軾在眾多的三國人物中,尤其嚮往那智破強敵的周瑜,故下片由「遙想」領起五句,集中腕力塑造青年將領周瑜的形象。作者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挑選足以表現人物個性的素材,經過藝術集中、提煉和加工,從幾個方面把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據史載,建安三年東吳孫策親自迎請二十四歲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將」的職銜,並同他一起攻取皖城。周瑜娶小喬,正在皖城戰役勝利之時,而後十年他才指揮了有名的赤壁之戰。此處把十年間的事集中到一起,在寫赤壁之戰前,忽插入「小喬初嫁了」這一生活細節,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見出周瑜的丰姿瀟灑、韻華似錦、年輕有為,足以令人豔羨。同時也使人聯想到:贏得這次抗曹戰爭的勝利,乃是使東吳據有江東、發展勝利形勢的保證,否則難免出現如杜牧〈赤壁〉詩中所寫的「銅雀春深鎖二喬」的嚴重後果。這可使人意識到這次戰爭的重要意義。「雄姿英發」、「羽扇綸巾」是從肖像儀態上描寫周瑜束裝儒雅,風度翩翩。綸巾,青絲帶頭巾,「葛巾毛扇」,是三國以來儒將常有的打扮,著力刻畫其儀容裝束,正反映出作為指揮官的周瑜臨戰瀟灑從容,說明他對這次戰爭早已成竹在胸、穩操勝券。「談笑間、檣櫓灰飛煙灰」,抓住了火攻水戰的特點,精切地概括了整個戰爭的勝利場景。據《三國志》引《江表傳》,當時周瑜指揮吳軍用輕便戰艦,裝滿燥荻枯柴,浸以魚油,詐稱請降,駛向曹軍,一時間「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詞中只用「灰飛煙滅」四字,就將曹軍的慘敗情景形容殆盡。試看,在滾滾奔流的大江之上,一位卓異不凡的青年將軍周瑜,談笑自若地指揮水軍,抗禦橫江而來不可一世的強敵,使對方的萬艘舳艫,頓時化為灰燼,這是何等的氣勢!蘇軾為什麼如此嚮慕周瑜?這是因為他覺察到北宋國力的軟弱和遼夏軍事政權的嚴重威脅,他時刻關心邊庭戰事,有著一腔報國疆場的熱忱。面對邊疆危機的加深,目睹宋廷的萎靡慵懦,他是多麼渴望有如周瑜那樣的豪傑,來扭轉這很不景氣的現狀呵!這正是作者所以要緬懷赤壁之戰,並精心塑造導演這一戰爭活劇的中心人物周瑜的思想契機。
然而,眼前的政治現實和詞人被貶黃州的坎坷處境,卻同他振興王朝的祈望和有志報國的壯懷大相抵牾,所以當詞人一旦從「神遊故國」跌入現實,就不免思緒深沉、頓生感慨,而情不自禁地發出自笑多情、光陰虛擲的嘆惋了。仕路蹭蹬,壯懷莫酬,使詞人過早地自感蒼老,這同年華方盛即卓有建樹的周瑜適成對照。然而人生幾何,何苦讓種種「閒愁」縈迴我心,還是放眼大江、舉酒賞月吧!「一樽還酹江月」,玩味著這言近意遠的詩句,一位襟懷超曠、識度明達、善於自解自慰的詩人,彷彿就浮現在我們眼前。詞的收尾,感情激流忽作一跌宕,猶如在高原闊野中奔湧的江水,偶遇坎谷,略作迴旋,隨即繼續流向曠遠的前方。這是歷史與現狀、理想與實際經過尖銳的衝突之後在作者心理上的一種反映,這種感情跌宕,更使讀者感到真實,也更能引起讀者的思考。
這首詞從總的方面來看,氣象磅礴,格調雄渾,高唱入雲,其境界之宏大,是前所未有的。通篇大筆揮灑,卻也襯以諧婉之句,英俊將軍與妙齡美人相映生輝,昂奮豪情與感慨超曠的思緒迭相遞轉,做到了莊中含諧,直中有曲。特別是它第一次以空前的氣魄和藝術力量塑造了一個英氣勃發的人物形象,透露了作者有志報國、壯懷難酬的感慨,為用詞體表達重大的社會題材,開拓了新的道路,產生了重大影響。據宋俞文豹《吹劍錄》記載,當時有人認為此詞須關西大漢手持銅琵琶、鐵綽板進行演唱,雖然他們囿於傳統觀念,對東坡詞新風不免微帶譏誚,但也從另一方面說明,這首詞的出現,對於仍然盛行纏綿悱惻之調的北宋詞壇,確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劉乃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