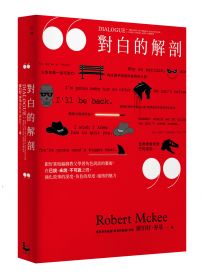對白不論於戲劇或敘述中,一概具有這三種基本功能:解說、角色塑造、行動。
解說
「解說」在此是術語,意思是將虛構的背景、歷史、角色等指明出來,供讀者、觀眾在某個當口吸收消化,以便跟上情節與入戲。作者在此有兩條途徑可以將解說嵌入敘述中:一是描寫,一是對白。
故事搬上舞台和大小銀幕,要由導演與眾多設計師將作者筆下的描寫轉化成對白之外的種種表達元素,例如布景、服裝、燈光、音效等。漫畫家和圖像小說作家要講的故事有圖為證。小說的作者就必須經由遣詞用字,以文學描述將文字意象投射到讀者的想像當中。
對白一樣具有這樣的功效。比方說,想像一下這個畫面:金碧輝煌、舖設大理石的門廳,一個個西裝革履的金髮男子在接待櫃台簽訪客簿,櫃台還配置了制服警衛,背景可見一具具電梯不時開合起落。乍然一瞥這樣的景象,立即說明了幾件事:地點-北半球某座大城市中的辦公大樓;時間-工作日,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之間;社會-西方文化的專業階級,雇用武裝警衛保護高踞層樓之上的高級主管,隔開街頭巷尾的貧民大眾。除此之外,掩蓋在這畫面下的潛文本,透露的是爭強好鬥、白人男性主宰的商業世界,追逐財富和權力,與腐敗只有一線之隔。
這時候,再想像某個精力旺盛的投資經紀人在和潛在客戶一起用餐,聽聽他怎樣以三寸不爛之舌大玩一語雙關的言外之意:「上去吧,看看我那批小老鷹。我們一夥人在七十七層樓上作窩,準備痛宰華爾街呢。」這樣的文字畫面連字素(grapheme)也用不到推特(tweet)限定的那麼多,表達出的層次卻比攝影鏡頭還要豐富。
凡是可以用畫面表達或直述說明的,幾乎都可以暗含在對白當中。所以對白的首要功能,就是把解說講給隔牆有耳的讀者/觀眾聽,而且不露痕跡。下述的規則,可視為這件困難工程的指南。
步調和時機
「步調搭配」(Pacing)是指「解說」嫁接到敘述當中的比率或頻率。「時機」(Timing)是指選擇哪一場景、在該場景中又要選擇哪一句台詞來透露某一件事情。
安排解說的步調搭配和時機,首先要考慮的風險是:給的解說太少,讓觀看的人一頭霧水,無法繼續入戲。但若是反過來,靜態解說一口氣給得太多,又會扼殺他們看下去的興趣:讀者會扔下手裡的書,觀眾則是在座位動來動去,叨唸著先前應該多買一點爆米花才對。所以,解說推送出來的步調和時機都要仔細考慮、巧妙布置。
因此,為了抓住觀看者,出色的作家都懂得把解說化整為零,一點一點放出來,唯有在觀眾或讀者一定要知道也想要知道的時候,才把他們非知道不可的訊息透露出來,半刻也不會提早,而且只給最少量,足以維持其好奇心、讓同理心不要中斷就好。
現代的讀者、觀眾看故事都看成精了,解說若是給得太多,不僅他們的反應會變得消極被動,連作者安排的轉捩點與結局都會搶在劇情之前被他們看破。這時他們當然會火大失望,瞪著眼前閣下的大作在心裡暗嗆:「我就知道是這樣。」所以,就如同十九世紀小說家查爾斯.瑞德所說的,你就是要「逗他們笑,惹他們哭,教他們等。」
最後一點,作者要解說的事在敘述當中未必每一件都同樣重要,因此也未必要等量齊觀。對此,不妨將故事中的每一件事條列存檔,從讀者/觀眾的角度排出輕重緩急,後來在改稿或潤飾時就會知道哪些需要強調,哪些需要加進不止一幕的場景裡去複述,以便讀者/觀眾後來在關鍵的轉捩點一定仍記得這些。其他沒那麼重要的,提示一次或比劃一下就可以了。
「演出來」相對於「講出來」
「用演的,不要用講的」(Show, don't tell),這一條原則是在警告作家不要拿靜態的解說去取代動態的戲。
「用演的」意思是寫出場景,搭配可信的布景,由可信的角色演出為了達成其欲求所作的掙扎,做的是斯時斯地會有的事,講的是合情合理的話。「用講的」就是強行要角色放下做到一半的事,改以長篇大論講出自己的生平或心裡的想法、感覺、好惡、過去、現在等等,看不出場景或是角色本身有什麼理由要來這麼一下。故事是人生的比喻,不是哲學的命題,不是環保的危機,不是社會不公,也不是角色人生的外在成因。
劇情出現這一類朗誦,多的是作者這邊的需求強行外加上去的,只為了把作者自己的思緒強行灌進被作者當作俘虜的讀者/觀眾耳裡,而非角色自然生成的行動需求。尤有甚者,潛文本還會被這種敘述硬生生抹煞。角色在種種對立之間掙扎,奮力要達成欲求之際,演員的聲音反應和手法會帶領讀者/觀眾去推斷演員沒講出來的意思和感覺。若是作者把找不到動機的解說硬是塞進角色的嘴裡,這些渾沌模糊的台詞反而會堵塞了連結看故事的人與說故事者內心的那一道門路。角色一旦壓縮為作者理念的發言人,讀者/觀眾看故事的興趣就會大減。
最後是,「用演的」會加快入戲的速度和劇情的步調;「用說的」反而會抵銷好奇心,拖慢節奏。「用演的」是把讀者、觀眾當作成年人,力邀大家入戲,鼓勵大家敞開情感迎進作者的想像,看進事物的核心,跟著一起邁向未來的發展。「用說的」則像是把讀者/觀眾當成小孩子,摟著坐在膝頭上,像父母說教那樣拿一目瞭然的事來細細解說。
下面這段話便是這樣的例子。當哈利和查理打開門鎖、往他們的乾洗店走去:
查理:「喔,哈利啊,我們倆認識多久了?有沒有—二十年?不只?我們從小學就認識了。很久了,是吧?老朋友,欸,今天早上天氣真好,你怎樣呢?」
這一段對白的目的,單純在告訴讀者/觀眾查理和哈利的交情有二十多年了,從小一起上學,而且這時候正是早晨。
下面這段話就不一樣了,而且這樣就叫做「用演的」:
查理打開門鎖,往乾洗店走去。一臉鬍渣的哈利穿著T 恤,身子斜靠在門框上,嘴裡叼著大麻菸捲,止不住格格傻笑。查理轉頭看他一眼,忍不住搖頭。
查理:「哈利啊,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肯長大?你看看你,還有那些什麼紮染襯衫,笑死人了。你二十年前在學校唸書時就是這一副幼稚的蠢相,到現在一點也沒變。你醒一醒啊,哈利,你聞聞你這一身臭的。」
讀者的想像或觀眾的眼睛會朝哈利轉過去,去看他被人這樣子糟蹋後有什麼反應,同時也神不知鬼不覺地順便把「二十年」和「唸書」這些事聽了進去。
故事中的每一件關鍵事實,都有它終究必須揭露的時刻,這時候就需要抓準緊要關頭一口氣送進去,製造恍然大悟的效果。這些事情和隨之引發的領悟傳入讀者/觀眾的意識時,絕不可以反而把他們的注意力從劇情的發展拉開。作者就是要有能耐一邊拉著讀者/觀眾的注意力朝某個方向前進,一邊把事情從另一個方向偷渡進來。
這一招瞞天過海需要擇一使用或同時並用以下這兩種技巧:「敘述驅力」和「解說彈藥」—前一種技巧攪和的是知性的好奇心,後者攪和的是感性的同理心。
敘述驅力
敘述驅力是我們看故事看到入戲時的副作用。劇情峰迴路轉,內情點滴透露,在在激得看故事的人忍不住要問:「接下去會怎樣?在這之後又會怎樣?這樣子下去會變怎樣?」一小段、一小段釋出的解說,從對白悄悄滲透到讀者或觀眾的意識背景裡,惹得讀者或觀眾忍不住好奇而伸出雙手,想要抓住一些未來的發展,牽引他走完故事全程。讀者或觀眾在必須知道的時候知道他應該知道的事,卻始終不覺得有誰特地講出什麼事要他知道,因為只要知道了一點什麼就急著再往下看。
舉例來說,有一部小說的篇名取自一份說明文件,解說的威力卻能蓄積出強大的敘述驅力,那就是《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作者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自創了這個名詞,意指官僚制度的陷阱將人困在邪惡的邏輯循環中無法脫身。
這個故事的背景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地中海的一處空軍基地。小說的主人翁約翰.尤塞里安(John Yossarian)上尉,在第五章裡向基地的軍醫丹尼卡(Dan Daneeka)醫生打聽一位名叫「奧爾」(Orr)的飛行員:
「奧爾是瘋子嗎?」
丹尼卡醫生說,「確實是瘋子。」
「那你可以要他禁飛嗎?」
「當然可以。但要他先來找我下禁飛令。規定是這樣子說的。」
「那他為什麼不來找你下禁飛令?」
「因為他是瘋子嘛。」但尼卡醫生說,「要是不瘋,怎麼會死裡逃生那麼多次還繼續出作戰任務。是啊,我是可以要奧爾禁飛,但要他自己來找我下禁飛令才行。」
「這樣就可以禁飛?」
「對,這樣就好,只要他自己來找我。」
尤塞里安問,「然後你就可以要他禁飛?」
「不行,那我反而不能要他禁飛了。」
「你是說這裡面有詐(catch)?」
「怎麼會沒詐。」丹尼卡醫生回答。「第二十二條的詐。有誰主動想要被禁就不是真瘋。」
這裡的詐只有一條,就是第二十二條。依這一條規定,遇到真實、立即的危險時會有擔心反應,是神智清楚才有的作用。奧爾是瘋子,應該要禁飛。他只需要開口要求就好;但是他一開口,等於在說他不是瘋子,就必須再飛更多任務。奧爾飛更多任務,表示他是瘋子,不飛,表示他不瘋。但他要是不瘋,就必須飛。他若想出任務,就是瘋子,就不用飛;但他要是不想飛,他就不是瘋子,那就不飛不行。尤塞里安對於這第二十二條使的詐竟然簡單得不得了,十分欽佩,吹了一記口哨表示真是要得。
「這詐還真是了不得,第二十二條的詐。」他有感而發。
「舉世無雙的。」丹尼卡醫生附和他。
請注意海勒怎麼把一段間接對白插進一幕戲劇對白的場景裡。從這一段文字概述,我們看到丹尼卡對尤塞里安說了什麼,尤塞里安又為什麼以一記口哨作回應。即使用的是第三人稱,為行文添了一絲權威評論的氣味,這一段仍然屬於「演」,而不是「說」,原因如下:(1)這一段出現在戲劇場景之內;(2)這一段將場景的動態往前再推進了一步;丹尼卡要尤塞里安不要煩他,不要再找藉口退出作戰行列,尤塞里安也恍然領悟到自己說自己發瘋純屬徒勞。丹尼卡透露的事成了轉捩點,將尤塞里安的計謀朝否定的方向推去。
就「敘述驅力」而言,讀者只要看懂了第二十二條軍規內藏的邏輯教人逃不出生天,心頭的期待就馬上往前躍一大步。讀者會心想:這樣一來,這麼荒謬的規定,尤塞里安或其他角色該如何才能從制度箝制的魔掌中逃脫呢?從解說透露出來的內情進而引發疑問,激得讀者/觀眾想尋求解答,這就是推動敘述的驅力。
解說彈藥
悄悄將解說塞給讀者/觀眾的第二門功夫,是要去勾起看故事的人投入感情。同理心/移情作用,起自這樣的念頭:「這個角色和我一樣都是人。所以,不管他要什麼,我都希望他得到,因為我要是他,我也會想得到這些。」看故事的人一旦覺得自己和角色之間有共性,不僅會把自己和角色劃上等號,也會把自己於真實人生會有的目的,套在故事角色的虛構欲求上。
移情的紐帶一旦把人綁得入戲,以解說為彈藥的技巧就可以這樣發威:既然你寫的角色知道故事的來龍去脈,知道自己怎樣、別人如何,讀者或是觀眾也必須知道這些才跟得上你要講的故事。所以,在角色掙扎著想要達到目的之時,作者必須抓緊關鍵時刻,安排角色拿自己知道的事來當作彈藥。透露出前所未知的內情,對入戲的讀者/觀眾而言等於有挖到寶的樂趣,它也會很快遁入看故事的人的意識背景裡。
以《星際大戰》(Star Wars)最早的三部曲為例來看。這三部片都扣在同一件事上:「黑武士/達斯.維達」(Darth Vader)就是天行者路克(Luke Skywalker)的生身父親。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 1944~)講述這個故事的難處,在於這件事應該在什麼時候拿出來說,又要怎麼說才好。他可以在第一集安
排機器人C-3PO隨便找個時候把R2-D2 抓過來說悄悄話,用這個方式來透露。「你可別跟路克說啊,他知道了準會氣炸了。那個達斯是他老爸呢。」這樣處理,觀眾當然接收得到,只是效用微乎其微,甚至還有一點搞笑。盧卡斯最後選擇的,是拿解說當作彈藥,去引爆三部曲最有名的一幕。
在第二集《帝國大反擊》(The Empire Strikes Back)的故事走到高潮時,路克作出英勇的決定,選擇面對黑武士決一死戰。光劍肅殺交鋒之際,大魔頭勢如破竹,落水狗左支右絀。對路克的移情,對結果的焦慮,就這樣把觀眾牢牢釘在那一刻。
依照傳統的劇情高潮,主角在千鈞一髮之際應該會急中生智,反敗為勝。不過,喬治.盧卡斯在雙方纏鬥不休之際,把他一直藏在潛文本內的動機放進來攪和:黑武士想要他這不像兒子的兒子加入他惡名昭彰的黑暗世界,卻左右為難,必須兩害相權取其輕:是要殺了自己的親生兒子,還是被親生兒子所殺。為了脫困,黑武士選了電影史上最著名的一手絕招來當解說彈藥,要兒子繳械:「我是你父親。」只不過他這麼一透露沒救得了兒子,反而逼得路克想一死了之。
深藏在前兩部片中不為人知的真相,突如其來嚇得觀眾既同情路克的處境,也擔心起路克的未來。身世之謎揭曉就是彈藥,炸出觀眾對深層性格和過去情節的後見之明,澎湃洶湧,五味雜陳襲上觀眾的心頭,為三部曲的最終回舖下了道路。
直接告知
用演的不要用說的,這一條金科玉律適用於演出場景中的戲劇對白。老練巧妙、直截了當的告知,不論在書頁、舞台或大小銀幕上,不論是敘述對白或第三人稱的旁白敘述,都必須發揮以下這兩大優點:速度和對位。
(1)速度。旁白可以把一大堆解說塞在簡單的幾個字裡,在讀者/觀眾心裡種下理解的種籽之後揚長而去。內心自語能在一眨眼的工夫之間,將潛文本轉化成文本。角色和自己說話,可以循自由聯想而隨意從一段記憶跳到另一段,或是從潛意識迸現影像一閃而過。這樣的段落寫得精采的話,足以在一句之內就帶動情緒,例如馬奎茲(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小說《百年孤獨》(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多年後,面對行刑隊,邦迪亞上校會再想起遠遠逝去的那一天午后,他的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輕描淡寫卻栩栩如生的直述舖陳—單憑一句話便勾勒出繁複、濃縮的意象。
然而,影像加旁白敘述這樣的手法淪為平淡乏味的解說,套用「然後⋯⋯然後⋯⋯再然後⋯⋯」的格式,卻在所多有。這就是因難就簡,拿好做的「直說」取代費勁的「演出」。複雜的人物角色要在電影、電視的對白場景中作戲劇呈現,確實要有過人的才華、知識、想像力,缺一不可。至於嘮叨累贅的敘述,只要有鍵盤讓你打字就行。
將敘述性解說轉化為戲劇場景,需要擇一應用以下這兩門技巧:
一,在場景當中插話。把「然後⋯⋯然後⋯⋯再然後⋯⋯」的直白報告,改為戲劇式的「我說/他(她)說」敘述場景,主述(不論是小說寫作、舞台演出,或是大小銀幕的配音第一人稱)可以一字一句覆述回憶當中的場景對白,或是利用間接對白來提示。
網飛(Netflix)的影集《紙牌屋》便會不時拿間接對白穿插到場景中。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飾演的法蘭克.安德伍(Frank Underwood),常會轉身直視鏡頭對觀眾講話,像大學教授在對學生上課講授政治權謀。下述的獨白,是安德伍以一段戲劇解說帶領觀眾一窺他的內心世界,順帶看一下叫做唐納(Donald)的這個角色。安德伍單憑兩句話就勾勒出生動鮮明的比喻,點出唐納其人的性格弱點:
烈士夢寐以求的,以利刃加身為最。所以,磨劍霍霍之後,就可以
高舉劍柄,找好角度,然後,一、二、三⋯⋯
下一拍,不出大教授法蘭克所預言,唐納自願成為安德伍知法犯法的替罪羔羊。
二,製造內心衝突。把自我之間的角力搬上銀幕,由作旁白的角色娓娓道出內心正反兩面的掙扎,範例可見以下兩部電影:尼可拉斯.凱吉(Nicolas Cage)在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穿梭鬼門關》(Bringing Out the Dead)中飾演的法蘭克.皮爾斯(Frank Pierce),或是鮑伯.克拉克(Bob Clark, 1939~2007)拍的《聖誕故事》(Christmas Story)當中尚.薛柏德(Jean Shepherd)出飾的成年版拉飛.帕克(Ralphie Parker)。
(2)對位。依照我的經驗,用敘述技巧為故事添色增光,效果最大的當推對位這個手法。有些作者不用主述來說故事,而是將故事全本寫成戲劇,再指派一名角色來敘述,牴觸或譏諷劇情的主題。作者或以詼諧機智來玩弄劇情,或以劇情來加強諷刺,或拿私人和社會作對位,或拿社會和私人作對位。
例如約翰.符傲思(John Fowles)的後現代歷史反小說(antinovel)《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這部長篇小說有一半篇幅在寫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士紳查爾斯.史密森(Charles Smithson)與有蕩婦之名在外的家庭教師莎拉.伍卓(Sarah Woodruff)之間的感情牽扯。不過,這則故事穿插了另一人作主述,他對於十九世紀的文化和階級衝突具有現代人才有的知識見解,在暗地裡侵蝕查爾斯和莎拉的戀情。經由一次又一次的對位,這個主述主張女性身在十九世紀要是沒有身家財產,追求到的痛苦多於愛情。
其他的例子尚有《你他媽的也是》,當中的配音旁白不時在提醒觀眾墨西哥社會的疾苦,作為這一齣成年禮電影的對位。伍迪.艾倫在《安妮霍爾》中的詼諧配音,相對於主人翁的自問自疑,也是對位。薩繆爾.貝克特寫的舞台劇《戲》(Play),三個角色分別埋身大甕只露出頭部直視著觀眾,各自口述腦中看似突發的隨想,就形成了三角對位。
作者想走明白直說的路線,小說是最天然的媒介。作家寫長、短篇小說,可以隨心所欲把解說明明白白擺在最突出的位置,愛寫多少頁隨他們高興,只要他們的文字功力足以虜獲讀者、滿足所需即可。例如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寫《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一開場就迸出一段
對位解說,牢牢勾住讀者的好奇心:
那是最好的歲月,那是最壞的歲月,那是智慧的年代,那是愚昧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日,那是絕望的冬季,我們眼前應有盡有,我們眼前一無所有,我們正直奔天堂而去,我們正直奔地獄而去⋯⋯
請注意,狄更斯用了全知的第三人稱主述,卻使用「我們」一詞,像是伸手攬上讀者的肩頭,把讀者帶進述說當中。勞夫.艾利森(Ralph Ellison)寫《隱形人》(Invisible Man),一開頭便以第一人稱的「我」說出一長串疾促的話,可以拿來和《雙城記》作比較:
我是隱形人。不,我不是說我是艾倫坡(Edgar Allan Poe)筆下那種陰魂不散的鬼;也不是你們好萊塢電影裡的那種靈體(ectoplasm)。我是有實體的人,有血有肉,有筋骨會流淚——搞不好還有人說我有心靈。我是隱形人,麻煩你們搞清楚,純粹是因為大家都不肯看到我這個人。就像你們在馬戲團的串場節目中有時候會看到的那些沒有身體的頭一樣,我的身上彷彿包裹著那種會扭曲影像的玻璃鏡面。大家靠近我的時候,只看到我周遭的事物,只看到他們自己,只看到他們想像出來自以為是的東西—總之,管他什麼都看得到,就是看不到我。
狄更斯和艾利森在後續的章節裡,將所有事件與場面都寫成戲劇表現,但有些小說作者不這麼做,而是一頁接一頁直述下去,沒將任何事件寫成戲劇場景。
想像一下,若是換成你來寫,前面引述的這兩段文字,要怎樣改寫成戲劇場景、以對白來演出?按理說應該可行。莎士比亞大概就做得到,問題是,要費多大功夫?寫給讀者看,直說可能有奇效,但寫給演員去演出,情況可就反過來了。
解說用在舞台和大小銀幕的表演藝術中,理想中應該是要透過講出來的話來傳達到觀眾那邊,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如前面所述,解說要做到不露痕跡,這樣的功夫需要耐心、天份和技巧。三者缺一,沒耐心、沒創意的編劇就會強行將解說塞給觀眾,還妄想觀眾會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