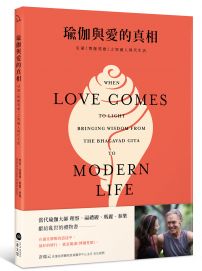第一章 良知和危機的兩難
想像一下,在又長又深又舒服的睡眠後,你於早晨醒來。深吸一口氣、伸懶腰、打了個大哈欠,你逐漸進入這一天。但是,接著你聽到遠處憤怒的鼓譟聲。集中注意力,你辨認出熟悉的聲音在謾罵,穿插嘈雜的腳步聲、咳嗽聲、笑聲和閒聊聲。光線比平日此時明亮甚多,你逐漸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在床上,四周是泥濘的道路,身邊還有一大群人盯著你醒來。
你和最親密的朋友在一起,處於混亂對峙的中心,局勢顯然一觸即發。你的朋友似乎很鎮定、清明、堅強,但是你被懷疑和恐懼的浪潮完全淹沒,感到汗涔涔、噁心與呼吸困難。你捏了自己一下,看看能否逃離現場,這一定是場噩夢。但是你仍在這裡!這不是夢,不是錯覺,也別無出路,如果不盡快採取行動,你知道自己即將死於戰爭中。
戰場的一邊,你看到摯愛的家人、親密的朋友和社群內受人尊敬的成員。另一邊是你的遠親,與這些年來你的老師們。你憶起這個衝突是源起於既有的政治歧見。而你曾以為能夠透過談判解決的衝突,現下已變成迫在眉睫的戰爭。克服困惑、悲傷和恐懼後,你很明白這不是夢,你前所未有地警醒於危機的中心,岌岌可危地立於行動與否的懸崖上。
無論所做為何,我們所敬愛的人都會被殺死,這可怕的局面遠比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極端情況更為嚴峻。然而,陷入任何危機時,我們同樣會經歷感覺無法克服的難題:家庭爭執、緊急情況、苛刻的工作環境,或受到他人的攻擊、虐待或冤枉指控。當面對任何兩難的推擠和拉扯,尤其是當領悟到生活的無常、牽一髮動全身的生命本質時,我們可能會浮現困惑、悲傷和絕望的感受。對於應該採取何種行動,很難有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相反地,當愈仔細審視所遇到的困境,我們愈清楚自己有諸多可行的選擇,而其中也必然會有互相矛盾之處,但是要走出去就必須選擇一個方向。
覺醒的旅程,開啟
處於分裂的情況下而且必須採取果斷行動時,我們就來到了岔路口──有機會「醒來」並全然投入生活經歷,體驗互相依存的關係。如果我們因應狀況並鬆綁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傾向(即使只是片刻),就有機會獲得洞見,也或許能顧全大局的伺機而動,而非被慣性的模式、自我中心與妄自尊大的意圖而驅使。
然而,在這些緊要關頭中佔上風的,往往是懷疑、恐懼和困惑,我們通常忍不住衝動地逃避困難,再次沉睡於自我的舒適妄念,自視分離或高於一切—認為自己的存在是全然的獨立現象,顧自扮演渺小故事的主角,甚至活在想像中的個人祕密小宇宙。而這正是在Gītā史詩的開端,主角阿周納的處境。他開始了一段覺醒的旅程,思考著:「我的人民(軍隊)和般度之子們狀況如何?集結成群,渴望在法和行動之域而戰?」(1.1)
許多印度文本或教導,會在起始時(有時甚至是開頭的字句)提點經文要旨的線索,而Gītā的第一節詩句也是如此。當阿周納進入正法與行動之域(dharmakṣetre kurukṣetre),他訝異地看到兩方敵對軍團,全副武裝地準備為王國的權利而戰。阿周納與他的好友戰車御者奎師納共乘一車,他血脈賁張,想像著在戰爭中履行責任的快感。身為一名戰士或統治階級──剎帝利(Kṣatriya),他畢生的準備就是為了此刻。我們可以想像他抽出他可靠的弓,撥弦測試確保校準。他聽到敵方在遠處吹響了數以千計的海螺,因此他和奎師納也吹響了他們的海螺,昭告戰鬥就緒。
而於此同時,阿周納也更清晰地看見了整個場景,他猶豫了,要求奎師納將戰車駛到雙方陣營之間,以便更仔細地評估局勢。他看到朋友、家人、老師和親信們排成一列,組成他的陣營。他很快意識到,敵方陣營中也有許多親戚,以及他敬佩和愛戴的人。想到所有人都將上陣廝殺的恐怖局面,阿周納的手掌汗涔涔、開始發抖,他感覺雙腿顫抖、皮膚似火燒、嘴巴乾燥、毛髮豎起。
從故事一開始,阿周納就意識到心慌意亂,渾身不對勁。如果他們獲勝,他的兄長會成為國王,阿周納的權力將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是,他並不想「在戰爭中獲得勝利」。反之,他知道殺戮毫無意義,傷害他想與之共享國土的朋友和家人是荒謬的。他看破了權力和財富的誘惑,而這對任何人來說都難以抗拒,尤其是有關個人利益的引誘。
好比說,假設你即將有份更好的工作,該職位需要經常出差並大量加班,但你想:「至少我會賺很多錢,並且能夠買得起大房子。」而後來你意識到,如果接受這份新工作,你將毀了與家人的關係,因為你永遠無法在家陪伴他們。你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二十小時,飛到世界各地。你可能覺得自己很特別,對自己擁有的職位、財富和權力感到非常滿意,但那些你欲與之同享大房子和上流社會的人,卻將覺得痛苦。
因此,就像是這份新的工作,Gītā一開始的教旨展示出──所有這些爭取主權的計劃,肇因於小我所欲求的某種王國,而征服的行動,終將破壞我們的關係,與共享成果的初衷。這是現代唯物主義者經常遇到的情況。在世界各地,眾多文化中的人們在經濟上獲致成功,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但卻破壞了人際關係。他們何樂之有?「噢!我的現代豪宅有私人游泳池。太遺憾了,我已經離棄了所有的朋友,也沒有人會來拜訪。我孤獨一人。」
同理,隨著全球推動無限經濟擴張,人類其實也在破壞這個允許我
們享受的環境。如果我們決定使用工業化農業來種植更多的糧食,破
壞環境,使無數代子孫無法享受高品質的食物或生活,那麼我們就是
目光短淺且相對愚蠢的。為了獲得更多的自我欲求,任何破壞自他關係與所棲息之地的有機體,都將自食惡果。因此,從某種層面來說,阿周納實際上看到了這種源於小我的自我實現方法,是有害且愚蠢的。他抵達戰場,立即意識到關係的重要性。阿周納不為私利著想。他領悟愛。他的直覺告訴他,這種情況絕對是錯誤的。然而,由於他的文化、成長經歷與懷疑,他無法信任自己的直覺。
阿周納告訴奎師納,如果他們上陣,他預見的是惡兆和不義的結果。在這種痛苦與巨大的衝突下,即使阿周納的心明瞭戰爭是不道德的,他卻也牢牢地執守於自己戰士的身分,因此陷入了兩難。他應該殺人嗎?他問自己:「天啊!我們竟然決心犯下滔天大罪,為了貪圖王國之樂而殘殺自己的人民。如果持國(Dhṛtarāṣṭra)之子們用武器殺了我,我也寧可手無寸鐵,不會抵抗,這對我來說將是至福。」(1.45-46)了解戰爭毫無意義,阿周納告訴奎師納,宣稱他寧願死於和平主義,也不願殺人。在這裡,第一章接近尾聲,曾經充滿活力的年輕戰士倒在戰車的座位上,弓從手中摔落,因不確定性而凍結,無法行動。
請記住,在印度神話中,弓箭代表著和諧的身與心。心智就像弓一樣,射出思想的箭。透過瑜伽體位法(āsana)、冥想(meditation)和調息法(prāṇāyāma)來調節身體的氣(此即感知,prāṇas),心智就會逐漸清晰,靈活地遊走於思想與反思、痛苦和冷靜、行動和不行動之間。透過這個專注又饒富彈性的心智,我們的思考也會益加精確,銳利智慧和專注的箭,從而清楚如何採取善巧的行動。而Gītā的故事,就從阿周納全然的混亂中起始,展開了他靈性、智慧和個人等層面的覺醒。
這正是為何神話的場景設置於法(dharma)與行動的戰場。法這個詞有很多含義,但在此脈絡中,首先它表示責任或法性職責的範疇,即阿周納應該做的事情。此外,它也代表理想或概念的領域,以及結構、認知和技術所涵蓋的疆域。法可以指根本教旨或事物的宇宙秩序,它定義了人在世上的個人目的,並隱含了明辨力,以指引德行。當我
們對自己的目標或法性職責非常熟悉時(它必須是由我們自身的狀況所定義),便能開始看見存在的終極結構,是恆變的也永遠根植於關係之中的。當我們培養了融入脈絡的智慧,就自然而然地生起仁慈、相互連結與慈悲的行為基礎。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法就是連結萬事萬物的凝聚膠。
另一個戰場的特性是行動:阿周納應該做什麼,又或者一旦確定某種情況下的行動方針之後,我們到底該怎麼做?無論我們在衝突或情境的細節中多麼煎熬,不管如何謹慎權衡最佳的行動方案,直到真正邁出第一步時,我們的行動才算數。這一步是真相揭露的時刻,在付出努力之後,成功或失敗才見方曉。當然,在我們全力以赴的行動之際,等同重要的是保持專注和警醒,傾聽回饋,明辨出適當的下一步(有時與起初設想的最佳方案完全相反)。例如,假使你是汽車、車輪或輪胎的設計師,直到汽車實際上路被測試之前,一切都沒有意義。
如果輪胎飛散或汽車撞成了熊熊火球,你就會意識到設計不正確且必須重新設計。因此,行動之域(kurukṣetra)指的不僅只是行動,更
精確地來說,是邁入行動時的明辨力。這代表因時制宜的行動:穩定覺知於你的道德基礎上(即你的生命意圖),使你的動機和行動能夠反映並順應意圖。如此一來,你會清楚地知道,在每個當下特殊的行動方針,以及相對應的適當時機點。
覺醒時必然要面對的危機
在這個非比尋常的場景中,Gītā揭幕了,如此重大的對質勢在必發。這些要旨不會設定在如玫瑰園等的田園美景,而是刻意設定在戰場。這種極端的局勢代表著每個人真正開始覺醒時所面臨的危機,當置身於世上錯綜複雜的關係之際,我們以開放的心智與坦誠的胸懷來回應難題。仔細觀察,我們發現實相、知識、耐心、行動、信任、仁慈—愛的本身,都是行動的指引。屆時,我們開始覺醒,而如果夠幸運,我們依止於所謂法與行動的疆域,或者一個能和諧法與行動的架構,心住於法而行。而事實證明,誠如Gītā中所教導的,在所有人皆面對的困境中,無論任何情況,我們的行動都被不能簡化成單一的法或單一的公式、技巧或風格。然而,我們仍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邁出關鍵的第一步。
雖然Gītā中的奎師納是老師,卻是由拒絕戰鬥的阿周納提出了初步深刻的教旨,理應撼動人心。然而,奎師納立即指正阿周納的猶豫完全肇因於無知,從而以更有趣的方式確立了要旨。身為讀者,大多數人一開始都應和阿周納對貿然衝入戰場與無情殺戮的抗拒,尤其對那些已練習瑜伽一段時間的人特別是如此,因為我們認同帕坦伽利(Patañjali)在瑜伽經中提出的第一則持戒(yama)(或道德原則)──不傷害。
我們已經更加柔和,對他人更寬容,更可能成為素食主義者,因為不願危害有情眾生。見到阿周納崩潰,丟下心愛的弓,並暴露他的脆弱,宣布自己不願意殺戮,奎師納不但沒有嘉勉阿周納是個優秀的瑜伽行者,卻是露出燦爛的笑容說:「你一面談論智慧,而另一面卻又悲傷那些你不該為之悲傷的人。智者不會為生者或逝者而哀悼。」(2.11)因此,奎師納一開場就非常惹人厭,這也很有趣。故事為什麼如此刻畫奎師納?出於這個原因,許多學者(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都如此)都屏棄了Gītā,因為他們認為奎師納和Gītā鼓勵無謂的殺戮。乍看之下,奎師納的確是建議阿周納漠視自己的良知—他的道德標準,強力武裝他起身戰鬥與廝殺。的確,他告訴阿周納,在戰場上殺人並不重要,因為一切都是無常。總之,他們無異於死。「那些自認殺人者與那些認為有能被殺者;兩者皆無知,祂不會殺也不會被殺。若瞭知此乃不滅、永恆,無生、無毀的人,能夠殺誰?誰能被殺?」(2.19;2.21)思考接下來的全文所傳達的啟示,很顯然,奎師納要
教導的要義極為複雜,不僅僅是鼓勵阿周納盲目履行自己身為戰士的職責而進行殺戮。
如果我們過於執著於細節──Gītā的神話故事,那麼就很容易忘記,這個教導旨在為所有人獨特之處境所提供指引。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任何人面對危機時都會發生的內在衝突,而在危機時刻,我們都必須起身迎戰。從隱喻的角度來思考Gītā,我們可以想像自己的身體即是一生中承載我們的戰車。奎師納代表我們的智慧──覺智(buddhi)和理解複雜情況與其緣由的能力,因此,根本上,他代表純意識(paramātman),在印度神話中被視為是「至上或原始的大我」。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我們內在的奎師納是見證者、朋友、摯愛──他者。在神話傳說中,他駕駛著戰車,而戰車代表阿周納的身體。拉戰車的馬匹象徵感官,而胸有成竹的奎師納掌握著韁繩,代表著心智統御當下感官的必要性,以免被四處拉扯。既為純意識,奎師
納代表著智慧,而且他選擇與阿周納的現況合作──阿周納真誠、熱切,對理解世界開始有更深刻的醒覺,但目前仍受到思想和感官的束縛。與其扮演上帝這個強大角色,或者扮演一個強迫推銷傳統、教條甚至真理的老師,奎師納選擇了僕人和嚮導的角色。這本身就是個教導,對吾等有興趣成為老師的人來說特別受用。
吹響海螺,回到當下
阿周納代表所謂的自我或自我意識,稱為Jivātman。我們和他一樣,都非常熟悉個人的自我意識,因為這是我們獨特的思維建構能力,包括微妙或粗略的思緒、欲求和厭惡,以及身體、心智和感官間的互動體驗。自我意識是我們想像中的真正自我,肉體接續著肉體、此生到來生、各種境遇的流轉。它不斷提醒著我們在具相世界的獨特體驗,而同時,這種體驗也必需與較為隱微的、直覺的、神祕的、無常和相連性的無我感知,對話交流。當我們在兩種體驗之間找到平衡時,也就是我們既作為個體生命(即jivātman),又作為超越肉體和想像的自我(即paramātman,至上意識)之共同存在,於是認同與分別心的掙扎便開始消退,而這就是隨著故事進展,逐漸發生於阿周納身上的狀況。
奎師納陪同阿周納來到戰場,他準備引導親愛的朋友再次憶起、重新熟識他的所知──與生俱來的人性和本自具足的慈悲心。如此一來,從一開始,奎師納也教導我們所有人,透過直接體驗全面的相連,而非透過理論與疏離的教條,來找到自己根本的真實、意義和真誠的慈悲(我們的法)。
至於如何將Gītā的教導運用到自身的經驗,從故事一開始,我們發現了兩個非常重要的隱含要旨。第一,是面對危機時保持清明的、具身的(embodied),與穩定扎根的重要性。當阿周納和奎師納進入戰場時,他們感受到了極大的振奮感,也就是今日我們說的腎上腺素激增。養兵千日,就是要用於此時!雙方成員吹響的海螺激動人心,表明戰鬥的開端,所以奎師納和阿周納也吹響了自己的海螺。
吹螺通常在印度傳統儀式中用來表示許多事物的開端或結束,大多在寺廟祭祀使用。此聲響是與大眾溝通的一種方式,可聚精會神。吹螺需要集中注意力與深長平穩地吐氣,其效果實用又立即的喚醒吹螺者。因此,由於音頻和吐氣的扎根效果,吹螺者必然沉浸於身體的覺受。無論是吹奏還是聆聽,海螺聲都會喚醒我們回到當下,重新聚焦游離的心智(我們的citta vṛttis)以及消弭注意力散亂的狀態,而這些狀態經常使我們無法活在當下。
Gītā的故事,在阿周納吹響了海螺後,教導也隨之展開。他猶豫了,要求奎師納將戰車駛至雙方敵營之間,想看看「那些為了滿足持國邪惡之子,集結成群、蓄勢待發的戰士們。」(1.23)
正是此時,阿周納開始提出質疑。也許他的猶豫是因為海螺的音頻使他回到身體的感知,而深長的吐氣使他連結地氣並回到當下,他的心瞬間變得平靜。此時此刻,他開始覺醒,而他覺醒的故事(我們的故事)也逐漸揭露。因此,從文本的一開端,我們學到了停頓的必要性,以專注於感官的內在體驗,找到沉穩於當下的方法。吹響海螺代表著相信我們全面、具體的經驗和直覺(良知),在面對危機和困境時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