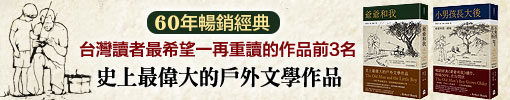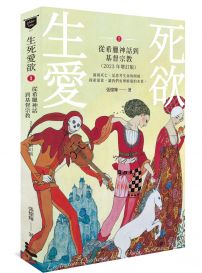【代序】(摘錄)
——劉保禧(撰)
I.
傳聞29歲是釋迦牟尼一生的轉捩點。那年,俗名「悉達多」、尚為太子的他外出王宮遊觀。在此之前,悉達多一直長於深宮,起居行止被父親限於王城之內。第一次出遊,在路途上,他遇上了一個老人,滿頭白髮,牙齒掉落,皺紋滿臉,身體傴僂,手持柺杖,步履蹣跚,氣喘不已。悉達多深感震驚,首次體驗到「老」是怎樣的一回事。他問隨行的侍者:衰老是否無人可以倖免?侍者答曰:「然。生必有老,無有豪賤。」太子聽後感到惆悵,無心遊觀,遂駕車回宮。心中默默想著:「念此老苦,吾亦當有。」
同年,悉達多第二次出遊,遇上了一個病人。聽到侍者解答:「生必有病,無有貴賤。」他感到惆悵,無心遊觀,遂駕車回宮。心中默默想著:「念此病苦,吾亦當爾。」
同年,悉達多第三次出遊,遇上了一個死人。聽到侍者解答:「生必有死,無有貴賤。」他感到惆悵,無心遊觀,遂駕車回宮。心中默默想著:「念此死苦,吾亦當然。」
這段佛陀的出遊經歷,道出了人的存在(human existence)問題。生而為人,無論種族、階級、性別,同樣無可避免老病死苦。無論生於二千多年前的印度,抑或活於今時今日的香港,亦復如是。換言之,這種「苦」內在於人的存在結構,超越了華夷、貧富、男女的限制,甚至是時間與地域的限制。就算我們不是佛門中人,也普遍地落入「苦」的網羅之中。佛教之所以偉大,首先在其原初的洞見,揭示「苦」之於人的存在,必不可免,「吾亦當然」。至於佛教如何回應人生之苦,有諸種教義與修行,此是後話。
自言在香港中文大學度過大半生的張燦輝,也是機緣巧合,著眼於人的存在問題。他在訪問中說過,父親在他讀大學第一年遇上意外喪生,令他頓感困惑:為何我們出生?出生了又要面對死亡?人生在世又有何意義?體驗他人的死亡,悉達多選擇了出家修道,張燦輝則毅然從香港大學建築系轉到中大哲學系,自此踏上哲學之路。
基於生命感觸而進入哲學領域的人,往往有一種浪漫的情懷,不按常理出牌。⋯⋯在大學任職教授,本來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關門研究,潛心寫作,發表期刊論文。偏偏張燦輝選擇一條「愚蠢」的道路,重視教學多於研究,在學生身上花費心力多於自己的著述。上他的課,課時總是超過原來時間最少半個小時,每周閱讀材料總是有過百頁,每年總是躍躍欲試開新課程拓展新的領域。至今七十有餘,講學著述不斷,背後承托著的是源源不絕的生命力。
事實上,有生命感觸,從「人的存在」探索學問,正是中大哲學系其中一個悠久的學術傳統。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談論為學之道,指出「知識」與「思辨」固然重要,但是兩者之外,尚有「感觸」──「必有感觸而後可以為人。感觸大者為大人,感觸小者為小人。曠觀千古,稱感觸最大者為孔子與釋迦。」不諳牟宗三學問者,讀其著述,見其動輒議論儒釋道、康德、海德格等東西學術,很容易就覺得混亂,迷失其中。這是因為不懂得閱讀牟宗三的心法,所謂「感觸」是也。正因為有所感觸,有著存在的感受,所以牟宗三看到的是儒家的「命」、佛家的「苦」、基督宗教的「罪」──綜而言之,都是人的有限性。 必須首先對生命有所感觸,然後觸目所及,無論是康德、海德格 ,或者羅爾斯的政治哲學 ,都可以是生命的學問。
不過,人皆可以對生命有感觸,對死亡有困惑,這些存在的感受不必然化為學問。感觸小者可以因一時興會,長嗟短嘆;感觸大者如釋迦牟尼,則因為洞見人世間的苦相,而有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等諸種教法。那麼,對生死愛欲有所感觸的張燦輝,所成就的學問又是怎樣的呢?
(⋯⋯)
III.
《生死愛欲》上下兩冊,共24章,加上導論、總結、附錄、後記,前後超過40萬字,而且論域廣闊,從儒釋道到唐君毅,從柏拉圖到21世紀的網戀,包攬古今東西。不過,一旦我們把握到前文提及的理論線索,從海德格哲學的一些關鍵詞著手,就不會迷失於《生死愛欲》的宏大論述之中。
第一個關鍵詞是「生命」。在1920年代,海德格相當推崇「生命的學問」,甚至「此在分析」也可以說是一套生命哲學:「生命 = 此在,這即是在生命中及透過生命而『存在』的。」後來他有某些理由刻意不再運用「生命」這個字眼,但是截至《存在與時間》,海德格的哲學仍然有濃烈的生命論者的氣息。
張燦輝亦然。從導言到總結,《生死愛欲》一直鞭撻抽離生命的學院哲學:「當然我們都是在大學做學院哲學的,本來是處理理論的問題,一生都是在哲學系度過的。但問題是,若果哲學僅是如此的話,究竟與我們的生活有何關係呢?」
前文提過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有一個「生命的學問」的學術傳統,有趣的是,張燦輝對此並非照單全收,他修正了前賢(包括老師勞思光)的說法。老一輩的學者有深厚的儒學背景,往往判斷中國哲學重德,是生命的學問;西方哲學重智,是理論的知識。 張燦輝卻發現,這個判別東西學術的區分,其實是站不住腳的。西方哲學亦有生命的學問,而且源遠流長。借助法國學者阿多(Pierre Hadot)的研究《哲學作為生活之道》,張燦輝從「生命」的角度重新閱讀西方的哲學史,指出所謂以「知識」為主題的西方哲學,大概只有三百多年的時間。從「生命」的角度切入,反而為東西學術傳統找到了接合點。
第二個關鍵詞是「世界」。勞思光最重視「主體性」的概念,幾乎所有著述都有述及。張燦輝很清楚老師的用心,曾撰文討論其「自我」理論。扼要言之,勞思光將自我境界劃分為三種:認知我(cognitive self)、情意我(aesthetic self)、德性我(moral self),即是一般所謂知、情、意的能力。在他看來,以上三種能力雖展現為三種不同的活動,但都統攝於「我」這個主體。論人生苦罪之不可免,以「承當精神」來展現「最高自由」,最後的根據還是「我」:「罪即是罪,苦即是苦,我仍是我。」在海德格的眼中,主體論者以「我」作為知、情、意乃至一切存在者的基礎,他嚴詞批判。究其關鍵,主體被視為「無世界的主體」(weltloses Subjekt, worldless subject)(SZ: 110),主體與世界成為一種對立的關係。我是我,世界是世界,世界只是我所認識的對象,甚或認為世界的存在由我的意識決定。海德格卻認為,我與世界並不是並列的,更不是先有我然後有世界,「作為存在者的此在,總已經在世界中了。」(SZ: 206)例如,是首先有一個足球世界,「我」才可以作為球迷,並以球隊作為我的鑑賞對象。「我」的鑑賞水平,由足球世界的評鑑標準──球隊戰術、球員技術──裁斷。足球世界非由某一個「我」主導,反而是每一個「我」,首先由「世界」這個意義網絡決定「我」之所是(球迷?球員?)以及不同存在者之間的關係(忠誠?敵對?)。
情愛現象的有趣之處,正在於它不可以(也不應該)統攝於某個單獨的主體。一段情愛關係,所說的不是「我」,而是「我們」。孤立分析「我」這個主體有何能力,並不能有效解釋情愛現象。同時,「我們」之間也不是主體與對象的關係,而是兩個主體之間的關係,亦即「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張燦輝就指出,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德愛」(philia)或是中國傳統的「情」,兩者都是相互性的,這樣才能夠培育彼此的德性或情感。不過,更重要的是,在兩個情愛主體之前,先有一個情愛的世界。每個人一出生,就被投擲於某個既定的世界,世界對「我」來說是被給予的(given),「我」就在這個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下生活。以香港的文化為例,如果我要表達讚賞之情,我應該舉起拇指,不應該舉中指;如果我要示愛,我應該送玫瑰,不應該送菊花。同樣道理,情愛活動的表現方式,並不是直接由我或你來決定。
在這個意義下,張燦輝以一種相當婉轉的方式回應了老師的主體論述。雖然勞思光學貫中西,但論其學術成就,公認是三卷四冊的《中國哲學史》評價最高。縱觀全書,勞思光以「主體性」為綱領,以「心性論」為中心,衡斷各家哲學的是非得失。《生死愛欲》亦有討論中國傳統,而且針對當代的中國哲學研究:
「在中國大部份的哲學討論中,均是集中討論性、情與心的關係,而情這個概念通常是指情緒或者是情感,但似乎是沒有討論人與人之間,如何產生「情」的問題。我們不禁要問:「在日常的人際關係中,究竟人是如何產生相思之情呢?」(第II冊,第13章)
在張燦輝看來,「集中討論性、情與心的關係」的學者(包括勞思光)的焦點是主體的能力──無論那種能力是認知、情意或德性──聚焦於個體生命,遺漏了「人與人之間」的「『情』的問題」。每一個人成為主體之前,其實先有一個世界,亦即「日常的人際關係」這個意義網絡。從主體性到世界,張燦輝巧妙地繼承並回應了老師的問題意識。勞思光為學高舉「主體性」,跟其特立獨行、睥睨俗世的為人匹配;學生卻嘗試告訴老師,還有一個有情世界,我們都是「與共存在」(Mitsein, being-with)。唯其如此,才有這段可貴的師生情誼。
第三個關鍵詞是「時間」,具體點說,即是「歷史性」(Geschichtlichkeit, historicity)。對於哲學稍有認識的讀者,應該知道當代的西方哲學可以粗略分為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與歐陸哲學(continental philosophy)。前者出身的學者,對於後者往往取徑歷史的研究方式大惑不解。研究歐陸哲學的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就面對過這種質疑。他解釋說,歐陸哲學學者一般採取歷史的進路,因為他們普遍不承認「哲學」與「哲學史」的區分有真確性,他們認為哲學根本是歷史性的。克里奇利指出,這意味著兩點:
1.人類主體的徹底有限性,即沒有什麼在人類經驗之外的類似上帝的立場底參照點,我們的經驗可以由此得到描繪和判斷;或者說,即便有的話,我們對此也會一無所知。
2.人類經驗的完全偶然的或被創造出來的特徵。這就是說,人類的經驗完全是人類的,是由我們塑造和再塑造的,而這種創造的環境確定無疑地是偶然的。
第一點針對的是傳統的形而上學與神學研究。這種研究方式通常將人類經驗訴諸一個超越於經驗的領域,通常就是「上帝」。因為人類是有限的存在者,受限於空間與時間;而上帝是無限的存在者,不受空間或時間所限,乃是無處不在的、自有而永有。可是,自從經過《存在與時間》的洗禮,歐陸哲學對於「非時間的存在者」或「超時間的永恆存在者」深表懷疑。海德格解釋過,《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的書名,「與」(und)字隱藏著中心問題。這個中心問題,就是「存在」與「時間」的關連──「存在」不可以不通過「時間」來理解。因此,一切的存在者的存在,若然說是「非時間的」或「超時間的」,其實是不可解的。
早期海德格的探索路向,並不是徘徊於天人之際,將上下而求索,因為訴諸所謂「上帝」其實逾越了人的有限性;他的進路是通古今之變,揭示「存在」被遮蔽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即是以歷史學取代神學的地位。
第二點承接第一點的討論。既然論述主題不再是絕對而超越的上帝,那麼人就不再命定「是」(存在)上帝的兒女。不是神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而是人在某個歷史時空信奉了某個宗教因而相信了某種人的形象。那是偶然的(contingent)、人為創造的(created)。領悟了這一點,人就從「上帝」中解放了。人是自由的,可以是這樣、可以是那樣。誠如海德格所言:「可能性高於現實性」(SZ: 38)。
再將以上的文字「翻譯」一次,就可以理解《生死愛欲》的歷史性。為什麼探討愛的本質,需要談論愛的歷史呢?因為「愛的本質」與「愛的歷史」,兩者的區分未必有真確性。當我們以為可以直接把握愛的本質,很可能只是被當下的歷史時空所遮蔽。例如,「很多人都以為愛情必然是浪漫愛,只要理解甚麼是浪漫愛的話,就可以了解甚麼是愛情了,其實世間上還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愛。」「我們愛一個人,並不只是浪漫愛的」。也就是說,我們狹隘地將「愛」等同於「浪漫愛」,並且渾然不覺。然而,「浪漫愛」其實曲折地繼承了柏拉圖的欲愛(eros)與基督宗教的神愛(agape)。浪漫愛將對象純潔化、形象化、理想化,帶有強烈的柏拉圖主義色彩;浪漫愛也將基督宗教的「上帝是愛」(God is love)顛倒為「愛是上帝」(Love is god)──愛是最偉大的,令人克服一切,甚至跨越死亡(詳見第18章)。愛的歷史,讓我們更理解愛的本質。
這種歷史的研究進路,將情由形而上的領域拉到人間,亦即人的經驗領域。愛的研究,不再是傳統的形而上學或者神學,也無須預設「上帝」是愛的根源。《生死愛欲》沒有告訴讀者「真愛」是什麼,因為它根本無意提供一套關於「愛」的絕對標準,讓大家去遵從。本書更重視的是,如何從人的經驗出發,呈現「愛」的可能性──愛的類型是如此豐富多樣,有欲愛、德愛(philia)、神愛、浪漫愛,也有中國的「情」。人類的愛是自由的,可以是這樣、可以是那樣。愛的歷史,讓我們從獨斷與狹隘的狀態之中解放出來。
IV.
王家衛的《一代宗師》(2013),透過女主角宮二說出「修武的人有三個階段: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這個三階段說,我向來有自己一套海德格式的詮釋。
第一階段是「主體性」。無論是修武抑或習文,首要的是成就自己一套功夫。運歷代武學為己用,方為武者;納各家哲學於一身,才是哲人。首先以「自我」為座標,學習才有定向。所看到的不是一套套架構森嚴的功夫或學說,而是能夠入乎其中,將其拆解,然後出乎其內,為我所用。
第二階段是「世界」。武術也好,學術也好,都是一個江湖,最忌唯我獨尊。自我提昇之道,恰恰不是排斥其他門派,而是如何將之調和、融合。在電影中,宮寶森在金樓上,表示這輩子「只成了三件事」:(一)合併了形意門和八卦門;(二)主事中華武士會,並聯合了十幾個門派加入;(三)撮成了北方拳師南下傳藝。事實上,三件事只是一件事,就是調和融合各個門派,尤其是南北武術。類比來說,在哲學上,東西學術的調和融合,亦可作如是觀。不囿於東西南北,才見到武術與學術的天地。
第三階段是「時間」。電影中的一幕,宮寶森以前輩的身份聲言「咱們今天不比武功,比想法。」並讓葉問掰開他手中的餅。最後餅掰開了,葉問說出自己的想法:「其實天下咁大,又點止南北呀?勉強求存等如固步自封。喺你眼中,呢塊餅係一個武林,對我嚟講係一個世界。正所謂大成若缺,有缺陷先至有進步。真係洗得嘅,南拳又點止北傳呀?你話係咪呀?」無論南北西東,仍然是空間。南拳北傳,東西交匯,縱使突破了門派與地域的限制,但在時間的洪流的沖刷下,能否傳承下去,實屬疑問。後來宮二表示「我見過自己,也算見過天地,可惜見不到眾生。」因為宮二止於自己,止於南北合流,縱然曾經贏過葉問,但在武術的傳承上,卻是詠春做到開枝散葉。所謂「一代宗師」,不是由一個人獨霸武林,而是做到代代相傳。憑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
兜了一個大圈,我想說的是,以上就是我對於張燦輝老師的一些個人感想。
「生死愛欲」本來是一門課程,現在結集成書,誠為美事。但老師竟然囑我作序,除了感到惶恐,我亦大惑不解。畢竟他的學術圈子都是碩學鴻儒,論學問論輩份,怎樣也輪不到我。為何偏偏選中我?這道謎題,張燦輝老師沒有說破,總之就是要我作序。
在撰寫的過程中,我暗自忖度:這是一次學術回顧!不僅是他個人(主體性),而且是他的東西學術來源(世界),更重要的是,也是我這個學生的學術回顧,讓我領悟何謂學術傳承(時間)。閱讀《生死愛欲》的書稿,我看到他示範如何吸納勞思光與海德格的哲學,藉此踐行自己的哲學計劃。用勞思光的術語,那是「自由」;用海德格的術語,那是「本己」。在哲學的道路上,張燦輝見過自己,也算見過天地,最後用一本《生死愛欲》還諸眾生。我彷彿聽到老師在跟我說:這條路,我未走完,希望你能把它走下去。……
感謝老師囑我寫序,讓我可以「見自己」──我見到了我倆的師生情誼,也見到了勞思光與張燦輝的師生情誼。勞思光曾經說過,對於師道,只是為了解惑,非為傳道授業。我慶幸自己是張燦輝的學生,也慶幸勞思光是他的老師。師生之間雖有學術傳承,卻無須因循師說。在學術面前,大家都是自由的,無論研究儒家或海德格,重點在於哲學思考的能力,而不在於學說的傳承是否完整。因此,如果我真的做到「傳承」,恐怕原因不在於我是什麼「勞門」或者「海派」弟子,而是有朝一日,我也寫出了一部「我」的《存在與時間》。這才是對於老師最大的致敬。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