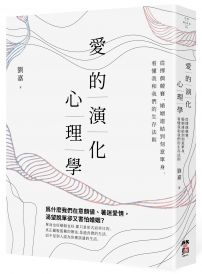科學有多種分類方法。如果以人類為科學的尺度,那麼與人無直接關係的是物理、化學這種關注日月交替、萬物演化的自然科學;如果將注意力向內翻轉,試圖理解我們內心世界的繽紛燦爛、愛恨情仇的科學則是心理學。「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又要去什麼地方?」是心理學的終極三問。
既然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那麼心理學需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必然是「我從哪裡來?」即什麼使我們成為人,而不是其他。
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的一個正午,人類學家唐納德.約翰森(Donald Johanson)在衣索比亞的哈達爾沙漠中,尋找能夠在人類和猿類之間架起橋梁的化石。突然,一塊略微突出地面、在陽光照耀下閃爍著光澤的肘骨化石,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塊化石與散布在它周圍的其他骨骼化石,構成了一副人形骨架。剛開始,約翰森以為這是一隻猴子的化石,直到他注意到骨架的膝關節,有直立行走必需的膝關節旋扭機轉。約翰森藉由鉀氬定年法,判定這副骨架屬於一種在三百二十萬年前直立行走於非洲大陸的生物。在晚上的慶功宴,那首一遍遍播放的披頭四樂隊的歌曲〈鑽石天空下的露西〉(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讓興奮不已的約翰森將這副骨架的主人稱為「露西」──目前已知最古老的人類祖先。
與其說露西是人類與猿類之間的過渡,不如說她是個起點,因為她的腦容量只有現代人的三分之一,與猿類的腦容量類似。那麼,究竟是什麼驅力促使人類大腦的容量在隨後的演化中增加了三倍?比較人類和猿類的大腦,我們會發現人類增加的大腦容量主要在額葉──從頭的外型來看,人類的額頭向前突出,飽滿豐盈,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天庭飽滿」。額葉的主要功能是處理複雜事務;據此,心理學家提出了「社會腦假說(Social Brain Hypothesis)」,即人類之所以需要更大的大腦,是因為人類所在群體的結構複雜度,遠遠高於其他物種所在的群體。
下圖呈現的是一般成年人的社交圈:「我」位在一系列不同親疏關係的圈層中心。離「我」愈遠,群體數量愈大,但親密度愈低。在「我」的社交圈裡,一百五十人的圈層是重要分界:由此向外,是更迭相對頻繁、與「我」無緊密關係的五百人熟人圈(同事、牌友等),以及也許可說出名字、記住臉孔的一千五百人圈層(如社交軟體的好友等);而在一百五十人圈層內,是自己信任、互惠互利,同時承擔責任的圈層(親人、朋友等)──源自我們祖先的家族與部落的大小。其中,居於核心的是與「我」一體的五人,他們與「我」相互纏繞、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他們定義了「我是誰」──這就是婚姻與家庭。
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獨有的現象。它的出現,並不是對愛的慶祝與永恆化,而是為了解決人類直立行走所帶來的生育問題。露西的骨盆變小,使得整個身體的重心更低、更容易直立;骨盆位置變高,以便髖部肌肉能在行走時穩定身體。但是,位置變高、尺寸變小的骨盆,必然使胎兒出生的產道變窄,導致難產。而演化提供的解決方案,是讓每個胎兒提前出生。如果人類胎兒像其他靈長類胎兒一樣發育成熟才出生,那麼他們需要在母體裡待足十八個月,而不是現今的九個月。所以,「早產兒」的存活與成長,需要母親全天候的照顧和父親持續的資源供給。因此,婚姻本質就是契約,一個男性與女性共同簽訂、讓早產兒得以成長、人類得以繁衍的契約。而契約是文明社會最根本的基石──基於契約,家庭組成部落,部落演變為城市,城市連接成為國家。複雜的社會群體由此而生,我們也從動物變成了人。
當露西從樹上爬下,在非洲大草原上直立行走時,未來人類的親密關係與愛恨情仇、社會文化的紛繁多樣與衝突妥協,就此展開浩瀚無垠的畫卷。這本書將聚焦在與「我」最關聯的親密關係:愛與性、婚姻與家庭。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由多個章節組成。每個部分各自獨立,可隨機閱讀。
第一部分從演化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美的定義,以及女性和男性的擇偶標準。在這章節中,我們將從基因的視角(第一章〈始於顏值:美的力量〉),解釋為什麼女性偏愛年長男性,而男性正好相反;為什麼女性最偏好的體型是沙漏形,男性則追求倒三角形;為什麼平均臉顯得美,而神奇的腰臀比○.七意味著什麼?更進一步,當我們擺脫演化在我們身上留下的印記,關注另一半的內在品質時,我們發現女性和男性的擇偶標準天差地別:女性要求男性有資源、有地位,要求男性上進、勤奮、成熟、穩定(第二章〈陷於才華:尋找白馬王子〉);男性則只求女性年輕漂亮,甚至這一點也可以放棄,見頁九十八「 零點效應」(第三章〈忠於人品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女性挑剔、男性寬容的背後,是女性擁有生育資源並在後代撫養中投入更多、是演化中的富人,男性卻一無所有。所以,男性為了與女性作為「富人」的「挑三揀四」抗衡,發展出馬基維利主義式的搭訕技巧(PUA);而女性為了對抗男性的「渣男體質」,報之以「紅杏出牆」,讓男性糾結於處女情結之中。換句話說,人類的演化史,本質上是男性與女性圍繞著後代繁衍的背叛與反背叛的歷史,難怪我們需要日益增大的腦容量來回應這零和賽局。但當我們的腦容量愈來愈大,理性與意識開始萌芽,行為更常被大腦的理性而非基因的獸性所驅動。於是,「我」開始成長為「我們」—在家族、宗教或法律的見證下,男性與女性正式進入了兩人世界:婚姻。
第二部分探討婚姻的前世今生。從演化的角度來說,婚姻只是繁衍後代的副產品,而非愛的昇華。但是,人之所以為人,是因人能超越演化的宿命,選擇自己的道路前進, 將婚姻與愛連接在一起。這時, 婚姻便從滿足生存需求的「制度式婚姻」演變成滿足安全感、愛與歸屬的「友伴式婚姻」,直到今天透過情感連結以實現自我表達、自我尊重和自我成長的「自我表現婚姻」(第四章〈安於陪伴:婚姻的本質〉)。然而,人類有文字記錄的歷史僅五千二百年左右,相對於約三百萬年的演化,我們還太年輕,犯了很多錯誤──誤認為激情之愛會澆灌出美滿持久的婚戀,而「包辦婚姻」只是歷史的遺毒。事實上,居高不下的離婚率並非現代人對婚姻的失望;相反地,這只是我們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表達我們的自由(第五章〈自我表達:我有我的自由〉)。當二十世紀下半葉,人類解決溫飽後,新的生活方式湧現—在穩定、富有安全感的生活之外,更要心理富足:一種充滿變化、跌宕起伏的非傳統、不穩定、不妥協的自我表現之生活。當心理富足的需求與婚姻相結合,伴侶的作用不再只是提供資源或者安全感,而是「因為你的存在,讓我想成為更好的人」。這時,有效溝通與真誠理解,成為保持穩定積極婚戀的關鍵。
第三部分以同理心為中心,講述自己與他人、自己與自己的溝通技巧。長久的親密關係並非伴侶花多長時間相處這般簡單,而是要用心經營(第六章〈化解衝突:經營愛情〉)。健康的親密關係應當是「安全依戀型」,即心意相通、性的親密、平等地給予和獲取情感與物質資源;更進一步則是積極的親密關係,需要自我表達並傾聽對方的困惑、感傷、喜愛和夢想,同時給予積極的回應。而這一切,就需要同理心(第七章〈同理心:你在,故我在〉)。同理心是高情商的表現,是建立連結,並非像同情心一樣,僅僅旁觀。同理心說明我們從他人的視角來看問題,並發現我們和別人的不同。同時,它可以幫助我們向內去認真聆聽自己、信任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我。透過保持好奇心、積極傾聽和轉換視角等方法,我們可以提升自我同理心,建立更為健康積極的親密關係;更重要的是,用同理心來傾聽內心的呼喚,讓我們找到美好的生活。
自從露西決定與古猿分道揚鑣,直立行走邁向未來的人類文明時,也許有個問題會縈繞在她的心頭:「成為一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
亞里斯多德說:「人天生是社會性動物。」的確,沒有一個人能夠自全、成為孤島。只有透過與他人的連結並形成親密關係,才有今天的人類,個體也更趨完整。但是,正如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說:「人本身並不複雜,複雜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密關係又帶來了背叛、衝突和創傷。
在美國作家瑪格利.威廉斯(Margery Williams)的童書《絨毛小兔》(The Velveteen Rabbit)裡,絨毛兔問他的好朋友老皮馬,怎樣才能變成一隻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兔子。
老皮馬回答:「真實並不能被製造出來;它只會自然而然地發生──當一個小朋友愛了你很久很久,並且他不只是想和你玩,而是真正愛你──那麼你就會變成真實。」
絨毛兔問道:「那我會受傷嗎?會痛嗎?」
「有些時候,會的。」老皮馬誠實回答道,「但是如果能變成真的,你是不會介意這些傷痛的。」
「那這是一下子就發生的嗎?」絨毛兔問,「還是一點一點慢慢地發生?」
「不會一下子發生的,」老皮馬緩緩解釋,「這需要很長的時間。這就是為什麼真實通常不會發生在那些或朝三暮四而輕易分手,或稜角鋒利而不知妥協,或敏感脆弱而需要時時照料的人身上。一般來說,等到真實終於降臨的那一天,你的大部分毛髮已經脫落,眼花耳聾,關節不再靈便,容顏也不再光彩如昔。但是,這都不重要,因為一旦變成真的,你就永遠不可能是醜陋的了,除非他不懂你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