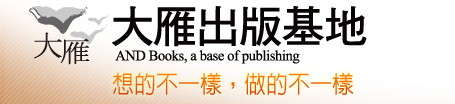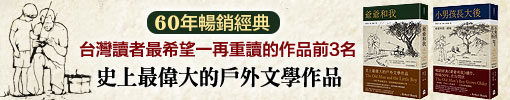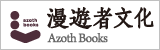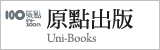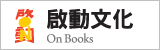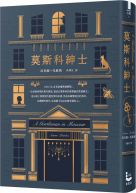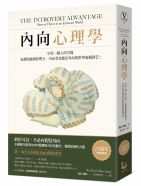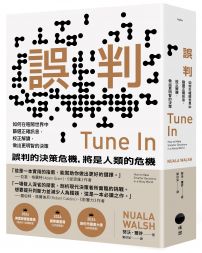第二篇:造成誤判的圍牆陷阱(節錄)
9. 道德陷阱:良心之亂
「假如你看見騙子卻沒說有騙子,那你就是騙子。」——黎巴嫩裔美國統計學家 納西姆.塔雷伯(Nassim Taleb)
「如果你知道自己一定不會失敗,你會做什麼?」這是十九歲的療診公司創辦人兼執行長伊莉莎白.霍姆斯放在辦公桌上的標語。
對史帝夫.賈伯斯的崇拜, 讓她傾盡所有心力創造「醫療照護界的iPod」。療診大肆宣傳他們的指尖採血診斷儀器,是前所未聞的創新突破——比競爭對手更便宜、更小巧,也更不痛。據稱儀器先進的「疾病地圖」,能偵測腫瘤指標、愛滋病毒和荷爾蒙異常。
霍姆斯的親戚說她一直想成為億萬富翁。她做到了——不到十年,全世界最年輕的白手起家億萬富翁就擁有九十億美元的身價,《公司雜誌》(Inc.)將她喻為「下一個史帝夫.賈伯斯」。
療診位在加州矽谷佩奇米爾路(Page Mill Road)一七零一號的辦公室,成為她心靈上的圍牆。霍姆斯的領導風格與吉姆.瓊斯如出一轍,要求員工無條件、無限制的忠誠。她的團隊「彷彿在建立宗教……所有不相信的人都應該滾蛋」。每一個層級的異議者都會被掃地出門。十五年來,公司文化充斥著機密和疑神疑鬼的氛圍。為了保護商業專有資訊,所有訪客都必須簽署保密協議,就連去上廁所都要專人護送。為什麼?因為愛迪生驗血儀可說是轟轟烈烈地失敗了。
霍姆斯無視病患可能遭受的風險,不斷宣稱儀器採用世界級的微流體(microfluidics)控制系統,並向職涯戰績輝煌的董事、參議員,以及包括喬治.舒茲(George Shultz)在內的前美國國務卿們,報告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她與經銷商巨頭的合作關係建立在誇大其辭與謊言之上。零售業龍頭沃爾格林(Walgreens)無視專家的警告,投資了一億四千萬美元,希望遠遠超越競爭對手CVS藥局。與此同時,許多療診公司的員工為了保住飯碗,都選擇三緘其口。
《華爾街日報》的記者約翰.凱瑞魯(John Carreyrou)接獲亞當.克雷伯(Adam Clapper)醫學博士,與喬治.舒茲之孫、療診公司的前員工泰勒.舒茲(Tyler Shultz)透露的消息後,揭穿了這個假技術的真面目,但為時已晚。管理失靈造成龐大無比的影響。投資人估計損失八億四百萬美元。二○一八年,霍姆斯被以詐欺和共謀罪起訴,必須在德州入監服刑十一年。
傲慢與野心之聲,經常取代良心和同情之聲。
本章將介紹五個致命的心理學盲點、聾點和啞點,它們都可能導致個人和組織忽略良心之聲、數十億元付之東流,甚至奪去性命。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太執著於目標,就可能導致正確的事情變成謬誤(有限道德〔bounded ethicality〕)。許多立意良善的領導者是以商業角度做決定,而非以道德出發(道德氛圍〔moral climate〕),並低估利益衝突的問題(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在這個時代,做正確的事會被忽略、良心被貶得一文不值(道德褪色〔ethical fading〕)。對此,有些人的彌補錯誤方式是展現善意(道德許可〔moral licensing〕),接著像修正主義歷史學家那樣合理化錯誤的行為(道德解離〔moral disengagement〕)。製藥產業、銀行業、製造業、法律界和運動界的眾多例子,說明了失職行為很容易與權力、情緒、自我結合,導致壓制了正確的聲音。
審理霍姆斯的案件時,戴維拉(Davila)法官很好奇這位「聰明絕頂」的企業家動機為何。「是狂妄自大……對名氣的病態執著……還是喪失道德準則?」她怎麼能哄騙這麼多聰明的股東?為什麼沒有更多董事和投資人察覺?他們是不是被眼前所見干擾,因而忽略聽見的資訊?各式各樣的聾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力量相乘效應。
▲說什麼良心?我在追逐目標
投資人、監管單位和病患都想相信最先進的技術真的有用——有限道德讓他們只聽見自己想聽的,以致沒有任何人察覺到被騙,而這符合我們在第二章提過的學者萊文的預設為真理論。對此,前療診公司的員工泰勒.舒茲解釋:「她真的很擅長告訴別人想聽的內容,才能讓騙局持續下去。她經常這樣告訴我爺爺……她告訴他很多……事實上根本是假的事情。」
充滿個人魅力的霍姆斯看起來也不像典型的詐騙犯。人們看見她的作風便不質疑她的本質,而這點證實了司馬賀的有限理性概念。此外,她的史丹佛學生身分非常有影響力,合夥人都對她刮目相看。
然而,療診公司的管理匱乏到了一蹋糊塗的地步。在一次取證過程中,前富國銀行董事和執行長理查.科瓦切維奇(Richard Kovacevich)回憶,董事會的作用比較像是提供建議,而非行使受託義務。「我不記得有人反對過她說的任何話……到頭來,做決定的都是她。」只有霍姆斯本人清楚公司的全貌。資訊不對稱,讓她得以掌控所有訊息。
由於醫療科技經驗不足,董事會只能欣然接受所有科學、營運和財務資料表面上的樣子。這個成功的故事實在太誘人,讓人無法質疑。
如同瓊斯鎮的案例,情境和時機都是功臣。一九九○年代的矽谷夢活過來了。臉書、優步、Spotify和Salesforce都創造了歷史。媒體不斷美化比爾.蓋茲和馬克.祖克伯等領袖人物,使得霍姆斯也希望得到加州帕羅奧圖(Palo Alto)科技圈的接納。
▲從花生到止痛藥
大部分的企業都是以商業目標為主要考量,但有些人做得太過火了。
二○一五年,美國花生公司(Peanut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執行長史都華.帕內爾(Stewart Parnell)假造安全合格報告,出售遭沙門氏菌汙染的產品。食安危機在全美爆發,九個人為此送命,數百人生病。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食品回收行動結束後,美國花生公司進行清算。帕內爾的律師告訴《時代雜誌》,他的委託人「做的正是其他花生食品業者也會做的事情」。帕內爾最終被以七十二項詐欺罪名起訴,被判處監禁二十八年,這是社會大眾對貪婪之聲的回應。
然而這樣做的不只有帕內爾。擁有普度製藥公司(Purdue Pharma)的薩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捐贈了數千萬元給慈善組織、羅浮宮的一個展廳、史密森尼學院的一座博物館和哈佛大學的博物館,且皆以薩克勒家族成員命名。但是,他們因為過度銷售止痛藥物疼始康定(OxyContin),被視為鴉片藥物危機的始作俑者,因此而留下不可磨滅的汙點。他們給業務員的獎勵沒有上限,更將業務員捧為「止痛英雄」。他們錯誤行銷疼始康定超過二十年,宣稱這種藥物的成癮率不到百分之一,最終導致約一百萬人因用藥過量死亡。
對此,儘管公司聽說有專門賣藥的攤位和成癮人數攀升的問題,他們依然選擇忽略。理查.薩克勒甚至怪罪用藥者。「他們才是罪魁禍首和問題本身;他們是不計後果的罪犯。」
最後,迫於輿論壓力,普度公司承認「知情且蓄意與他人共謀和達成共識,以及協助和慫恿員工在沒有合理醫療目的」的情況下販售產品。預料之中的是,他們表示對於公司利潤最高的藥物「意外捲入鴉片藥物危機」感到「誠摯地懊悔」,並與司法部達成協議,願支付六十億美元和解金。之後,牛津大學等學術機構,將薩克勒從各個紀念建築物中除名。
普度製藥公司有幫手。經銷商、連鎖藥局、醫師、行政人員和顧問都是共犯。CVS藥局和沃爾格林藥局(Walgreens)各支付五十億美元和解金,平息數千起官司;兩年前,嬌生集團則因對奧克拉荷馬州造成的傷害,支付了五億七千兩百萬美金。沒有人因此坐牢。
▲起因於利益衝突的脫序
貪得無厭的顧問也是一丘之貉。白領菁英主導的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曾向普度製藥公司建議如何提升銷售量。根據《紐約時報》報導,這「甚至發生在製藥公司二○○七年認罪之後……他們誤導醫師和監管單位,對疼始康定的風險產生錯誤認知。」令人震驚的是,麥肯錫顧問公司估算過,每位疼始康定用藥過量和成癮者的可能賠償金,只有一萬四千美元。
在未迴避利益衝突的情況下,二十二名麥肯錫顧問一邊建議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立法規範疼始康定的使用,一邊建議普度製藥該如何推銷藥物。這樣的利益衝突持續了十五年。到了某個階段,麥肯錫因為認定監管單位會疏於監督,甚至建議「摧毀我們所有文件和電子信件」。眾議院監督委員稱他們是「衣冠楚楚的運毒犯」,將利潤看得比「最高專業標準」重要,這群穿著愛馬仕華服的菁英就是利慾薰心。麥肯錫全球管理合夥人施南德(Kevin Sneader)坦承,麥肯錫並未「適切地認知到逐漸發生的濫用問題」,而他們的回應一如預期,想要「參與解決方案」。
但這樣的補救力道太小、也太遲了。
這是道德兩難嗎?麥肯錫從普度製藥身上賺了八千六百萬美元,又從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那裡拿到一億四千萬美元,令人咋舌。公眾輿論與法院之聲認定,他們必須為造成的損害負起法律責任——和解金為五億七千三百萬美元,可透過各項勒戒康復計畫來支付。
有違道德的不當行為,不只出現在商業界、收買新聞或政府合約,科學家也會為了達成目標不擇手段,罔顧良心之聲,比如,美國塔斯基吉大學的研究員對非裔美國人的剝削。
一九六○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彼得.紐鮑爾(Peter Neubauer)在雙胞胎和三胞胎一出生後就拆散他們,用來研究天生基因或後天養成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他從未向收養家庭透露實情,並將拆散手足的殘忍行為合理化為先進的科學實驗。直到被拆散的手足在鄰近的城鎮意外重逢,才揭發了他的所作所為。
雖然客戶有所要求,但是他們也不樂見專業的顧問、代理人、稽核員、治療師、教練或專項顧問做出違背道德的不當行為。然而,當牽扯到龐大金額、職業生涯和備受矚目的措施時,違反政策和利益衝突就難以避免。畢竟規則、罰款和懲罰的管轄範圍有限。
這並非新鮮事。想想看貓王艾維斯與帕克上校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吧!帕克這位處於衝突位置的非法移民,讓艾維斯三十逾年來只辦過三場國際演唱會。
你不能只仰賴自己所見的一切。
要提出問題,然後質疑答案。
▲有時做正確的事情可能是不對的
現代的顧客、員工和公民透過表達出對不公義的零容忍,以此期待官員、顧問和執行長做正確的事。監管人員和機構應該盡本分,讓犯錯的公司和人員負起責任。從很多方面來說,他們都肩負著如同第十二名陪審員一樣的責任,以致有時專業人士會面臨最艱難的兩難困境。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柯米(James Comey)就面臨了「布里丹之驢」(Buridan’s Ass)兩難。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前一個月,他得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因為從個人伺服器寄送機密信件而違反相關規定。這起案件的政治風險極高。所有高層人員在公開場合上都與政黨沒有瓜葛。假如柯米對這次調查保持沉默,會讓聯邦調查局看起來像選邊站;假如之後才公開調查,想當然耳他被指控是在替希拉蕊粉飾太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柯米公開調查案件,不論她是否真的有違反規定,都會讓形象可靠的候選人選情岌岌可危,如此一來,她的共和黨對手川普就能撿到便宜;同時,聯邦調查局和柯米都會捲入醜聞,被指控因為支持川普而產生偏見。
大選前三個星期,柯米告知國會這個消息,媒體因此掌握到了調查的風聲。
大選前十一天,聯邦調查局正式宣布他們正在調查希拉蕊。
大選前三天,他們證實希拉蕊沒有犯任何錯。
對許多人來說,這是道德上的正確決定,但在政治上卻錯得一塌糊塗。柯米被抹黑成川普勝選的推手。柯米聽了自己內心的聲音,卻低估情勢的嚴峻。他付出政治代價,儘管他手握大權,卻還是被川普開除。
總是有更大頭的熊存在!
柯米這個從黑手黨到美國富商瑪莎.史都華(Martha Stewart)都起訴過的男人,依然十分頑強:「將道德權威交給團體而壓抑自己的聲音,這樣是不對的……有道德的領導者會更忠於核心價值,而不是個人的收穫。」
雖然他做了正確的事,但其做出的決定會在更廣大的生態系統中掀起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這是否合理化了川普的外交政策髮夾彎、把移民兒童關籠,或國會山莊暴動事件?有些人認為不會。
這個世界不盡然是公平的,雖然許多好人一直在努力打造公平的世界,但壞人不總是會受到懲罰,好人也不見得總能得到獎賞。忙碌的人無法及時解讀訊號。
正義之聲聽起來很高尚,但不是總能保證得到正面的結果。我們再來看看有害的併購案。其實只要一直低著頭,就能幫助你躲過無可避免的斧頭。儘管如此,立意良善的員工還是經常會堅持指點新雇主如何做事——用以前的方法。雖然這種聲音會被忽略,掌權者還是會聽見一個訊息:「有麻煩了!」我看過許多同事勇敢發聲後,最後卻成為公司削減掉的「成本」。沒人想聽到別人告訴自己「你錯了」。
▲大家都是「好人」
就如前面討論過的,根深蒂固的優於平均效應(above-average effect)表示,大多數人不僅認為自己是更好的駕駛、舞者或決策者,也比其他人更誠實。人們對自己的道德準則感到很自豪,以致對自己想成為的樣子產生了浪漫的想像。話雖如此,多數人仍會為了搶得先機而誇大履歷、扭曲事實和說出善意的謊言。
價值觀有時會相互碰撞,即使在最高層級的地方也無法避免。
二○○四年,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安東寧.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拒絕迴避一起緊急政治案件,儘管該案件牽扯到與他一起獵鴨的好友迪克.錢尼(Dick Cheney)副總統。史卡利亞認為自己可以公正地主持庭審。雖然存在利益衝突,他還是告訴《洛杉磯時報》:「我不認為自己的公正性會受到合理質疑。」光是暗示就已經冒犯他的職業自尊。
第三任美國總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挺身而出,反對家庭奴隸貿易和販運奴隸至殖民地。雖然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的簽署者都公開支持逐步解放奴隸,但這些人大部分仍私下擁有非裔美國人奴隸。傑佛遜在蒙蒂切洛莊園(Monticello)蓄有六百名黑奴,其中包括莎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據傳傑佛遜與她生育了幾名子女。
傑佛遜聽見的是什麼聲音?公平與義務是否超越了情感依戀?他可能用理性推論合理化自己的雙重面向,以此抵抗認知失調。
如果付出代價的是其他人,同時看不見受害者,人們就更容易做出失職行為。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說「讓肥貓付出代價吧」(let the fat cats pay),也是為什麼騙子每五分鐘就會造假申請保險金,一年下來高達十二億英鎊。這是一種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而這會造成職場上的誤判。